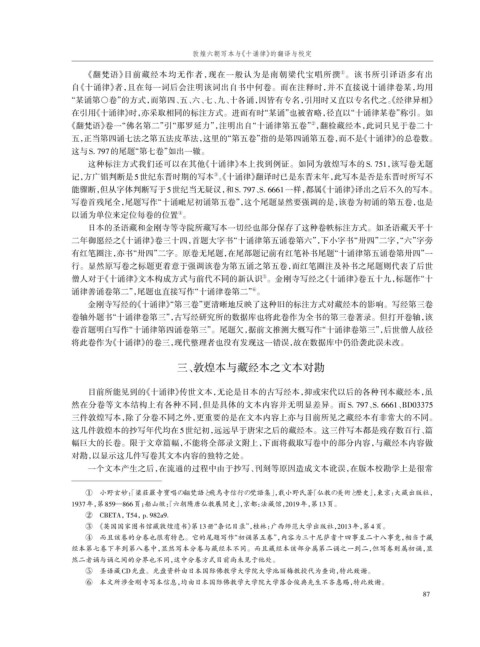Page 9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93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翻梵语》目前藏经本均无作者,现在一般认为是南朝梁代宝唱所撰 。该书所引译语多有出
①
自《十诵律》者,且在每一词后会注明该词出自书中何卷。而在注释时,并不直接说十诵律卷某,均用
“某诵第〇卷”的方式,而第四、五、六、七、九、十各诵,因皆有专名,引用时又直以专名代之。《经律异相》
在引用《十诵律》时,亦采取相同的标注方式。进而有时“某诵”也被省略,径直以“十诵律某卷”称引。如
《翻梵语》卷一“佛名第二”引“那罗延力”,注明出自“十诵律第五卷”,翻检藏经本,此词只见于卷二十
②
五,正当第四诵七法之第五法皮革法,这里的“第五卷”指的是第四诵第五卷,而不是《十诵律》的总卷数。
这与S. 797的尾题“第七卷”如出一辙。
这种标注方式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十诵律》本上找到例证。如同为敦煌写本的 S. 751,该写卷无题
记,方广锠判断是 5世纪东晋时期的写本 。《十诵律》翻译时已是东晋末年,此写本是否是东晋时所写不
③
能骤断,但从字体判断写于5世纪当无疑议,和S. 797、S. 6661一样,都属《十诵律》译出之后不久的写本。
写卷首残尾全,尾题写作“十诵毗尼初诵第五卷”,这个尾题显然要强调的是,该卷为初诵的第五卷,也是
以诵为单位来定位每卷的位置 。
④
日本的圣语藏和金刚寺等寺院所藏写本一切经也部分保存了这种卷帙标注方式。如圣语藏天平十
二年御愿经之《十诵律》卷三十四,首题大字书“十诵律第五诵卷第六”,下小字书“卅四”二字,“六”字旁
有红笔圈注,亦书“卅四”二字。原卷无尾题,在尾部题记前有红笔补书尾题“十诵律第五诵卷第卅四”一
行。显然原写卷之标题更着意于强调该卷为第五诵之第五卷,而红笔圈注及补书之尾题则代表了后世
僧人对于《十诵律》文本构成方式与前代不同的新认识 。金刚寺写经之《十诵律》卷五十九,标题作“十
⑤
诵律善诵卷第二”,尾题也直接写作“十诵律卷第二”。
⑥
金刚寺写经的《十诵律》“第三卷”更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旧的标注方式对藏经本的影响。写经第三卷
卷轴外题书“十诵律卷第三”,古写经研究所的数据库也将此卷作为全书的第三卷著录。但打开卷轴,该
卷首题明白写作“十诵律第四诵卷第三”。尾题欠,据前文推测大概写作“十诵律卷第三”,后世僧人故径
将此卷作为《十诵律》的卷三,现代整理者也没有发现这一错误,故在数据库中仍沿袭此误未改。
三、敦煌本与藏经本之文本对勘
目前所能见到的《十诵律》传世文本,无论是日本的古写经本,抑或宋代以后的各种刊本藏经本,虽
然在分卷等文本结构上有各种不同,但是具体的文本内容并无明显差异。而 S. 797、S. 6661、BD03375
三件敦煌写本,除了分卷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文本内容上亦与目前所见之藏经本有非常大的不同。
这几件敦煌本的抄写年代均在 5世纪初,远远早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这三件写本都是残存数百行、篇
幅巨大的长卷。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将全部录文附上,下面将截取写卷中的部分内容,与藏经本内容做
对勘,以显示这几件写卷其文本内容的独特之处。
一个文本产生之后,在流通的过程中由于抄写、刊刻等原因造成文本讹误,在版本校勘学上是很常
① 小野玄妙:「梁莊嚴寺寶唱の翻梵語と飛鳥寺信行の梵語集」,载小野氏著『仏教の美術と歴史』,東京:大藏出版社,
1937年,第859—866頁;船山徹:『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京都:法藏馆,2019年,第13頁。
② CBETA,T54,p. 982a9.
③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册“条记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 而且该卷的分卷也很有特色。它的尾题写作“初诵第五卷”,内容为三十尼萨耆十四事至二十八事竟,相当于藏
经本第七卷下半到第八卷中,显然写本分卷与藏经本不同。而且藏经本该部分属第二诵之一到二,但写卷则属初诵,显
然二者诵与诵之间的分界也不同,这中分卷方式目前尚未见于他处。
⑤ 圣语藏CD光盘。光盘资料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池丽梅教授代为查询,特此致谢。
⑥ 本文所涉金刚寺写本信息,均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落合俊典先生不吝惠赐,特此致谢。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