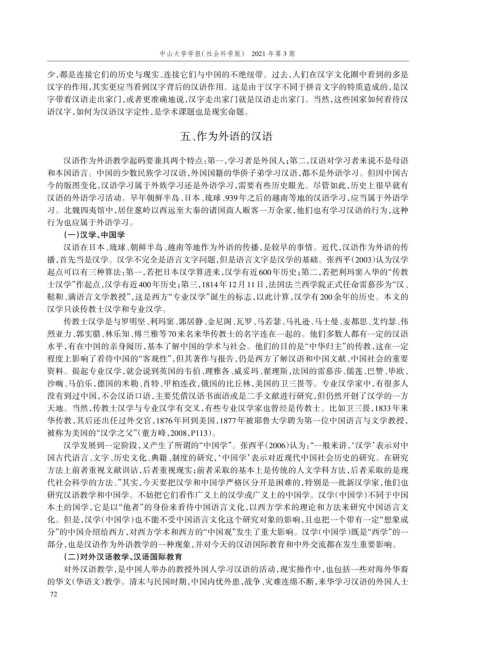Page 7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7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少,都是连接它们的历史与现实、连接它们与中国的不绝纽带。过去,人们在汉字文化圈中看到的多是
汉字的作用,其实更应当看到汉字背后的汉语作用。这是由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质造成的,是汉
字带着汉语走出家门,或者更准确地说,汉字走出家门就是汉语走出家门。当然,这些国家如何看待汉
语汉字,如何为汉语汉字定性,是学术课题也是现实命题。
五、作为外语的汉语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起码要兼具两个特点:第一,学习者是外国人;第二,汉语对学习者来说不是母语
和本国语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外国国籍的华侨子弟学习汉语,都不是外语学习。但因中国古
今的版图变化,汉语学习属于外族学习还是外语学习,需要有些历史眼光。尽管如此,历史上很早就有
汉语的外语学习活动。早年朝鲜半岛、日本、琉球、939年之后的越南等地的汉语学习,应当属于外语学
习。北魏四夷馆中,居住葱岭以西远至大秦的诸国商人贩客一万余家,他们也有学习汉语的行为,这种
行为也应属于外语学习。
(一)汉学、中国学
汉语在日本、琉球、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作为外语的传播,是较早的事情。近代,汉语作为外语的传
播,首先当是汉学。汉学不完全是语言文字问题,但是语言文字是汉学的基础。张西平(2003)认为汉学
起点可以有三种算法:第一,若把日本汉学算进来,汉学有近 600年历史;第二,若把利玛窦入华的“传教
士汉学”作起点,汉学有近 400年历史;第三,1814年 12月 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莎为“汉、
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这是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以此计算,汉学有 200 余年的历史。本文的
汉学只谈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
传教士汉学是与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金尼阁、瓦罗、马若瑟、马礼逊、马士曼、麦都思、艾约瑟、伟
烈亚力、郭实腊、林乐知、傅兰雅等 70来名来华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们多数人都有一定的汉语
水平,有在中国的亲身阅历,基本了解中国的学术与社会。他们的目的是“中华归主”的传教,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看待中国的“客观性”,但其著作与报告,仍是西方了解汉语和中国文献、中国社会的重要
资料。提起专业汉学,就会说到英国的韦伯、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斯,法国的雷慕莎、儒莲、巴赞、毕欧、
沙畹、马伯乐,德国的米勒、肖特、甲柏连孜,俄国的比丘林,美国的卫三畏等。专业汉学家中,有很多人
没有到过中国,不会汉语口语,主要凭借汉语书面语或是二手文献进行研究,但仍然开创了汉学的一方
天地。当然,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有交叉,有些专业汉学家也曾经是传教士。比如卫三畏,1833年来
华传教,其后还出任过外交官,1876 年回到美国,1877 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
被称为美国的“汉学之父”(董方峰,2008,P113)。
‘
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学”。张西平(2006)认为:“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
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
方法上前者重视文献训诂,后者重视现实;前者采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
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其实,今天要把汉学和中国学严格区分开是困难的,特别是一批新汉学家,他们也
研究汉语教学和中国学。不妨把它们看作广义上的汉学或广义上的中国学。汉学(中国学)不同于中国
本土的国学,它是以“他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语言文化,以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文
化。但是,汉学(中国学)也不能不受中国语言文化这个研究对象的影响,且也把一个带有一定“想象成
分”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对西方学术和西方的“中国观”发生了重大影响。汉学(中国学)既是“西学”的一
部分,也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一种现象,并对今天的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外交流都在发生重要影响。
(二)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是中国人举办的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活动,现实操作中,也包括一些对海外华裔
的华文(华语文)教学。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战争、灾难连绵不断,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士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