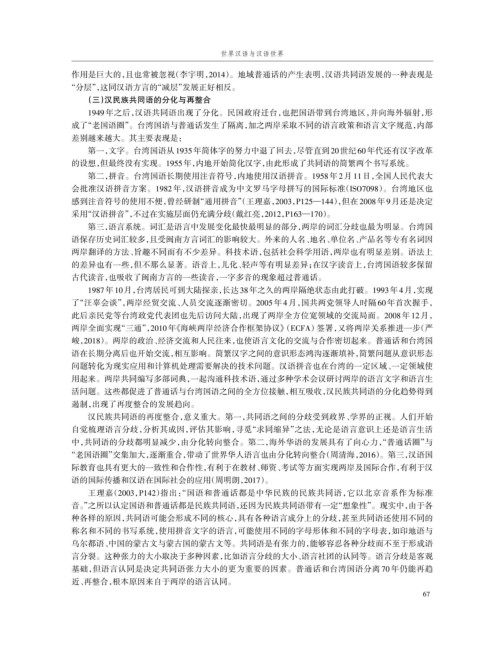Page 7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73
世界汉语与汉语世界
作用是巨大的,且也常被忽视(李宇明,2014)。地域普通话的产生表明,汉语共同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
“分层”,这同汉语方言的“减层”发展正好相反。
(三)汉民族共同语的分化与再整合
1949 年之后,汉语共同语出现了分化。民国政府迁台,也把国语带到台湾地区,并向海外辐射,形
成了“老国语圈”。台湾国语与普通话发生了隔离,加之两岸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文字规范,内部
差别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文字。台湾国语从 1935年简体字的努力中退了回去,尽管直到 20世纪 60年代还有汉字改革
的设想,但最终没有实现。1955年,内地开始简化汉字,由此形成了共同语的简繁两个书写系统。
第二,拼音。台湾国语长期使用注音符号,内地使用汉语拼音。1958年 2月 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82 年,汉语拼音成为中文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ISO7098)。台湾地区也
感到注音符号的使用不便,曾经研制“通用拼音”(王理嘉,2003,P125—144),但在 2008年 9月还是决定
采用“汉语拼音”,不过在实施层面仍充满分歧(戴红亮,2012,P163—170)。
第三,语言系统。词汇是语言中发展变化最快最明显的部分,两岸的词汇分歧也最为明显。台湾国
语保存历史词汇较多,且受闽南方言词汇的影响较大。外来的人名、地名、单位名、产品名等专有名词因
两岸翻译的方法、旨趣不同而有不少差异。科技术语,包括社会科学用语,两岸也有明显差别。语法上
的差异也有一些,但不那么显著。语音上,儿化、轻声等有明显差异;在汉字读音上,台湾国语较多保留
古代读音,也吸收了闽南方言的一些读音,一字多音的现象超过普通话。
1987年10月,台湾居民可到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由此打破。1993年4月,实现
了“汪辜会谈”,两岸经贸交流、人员交流逐渐密切。2005 年 4 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 60 年首次握手,
此后亲民党等台湾政党代表团也先后访问大陆,出现了两岸全方位宽领域的交流局面。2008 年 12 月,
两岸全面实现“三通”,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又将两岸关系推进一步(严
峻,2018)。两岸的政治、经济交流和人民往来,也使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密切起来。普通话和台湾国
语在长期分离后也开始交流,相互影响。简繁汉字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逐渐填补,简繁问题从意识形态
问题转化为现实应用和计算机处理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汉语拼音也在台湾的一定区域、一定领域使
用起来。两岸共同编写多部词典,一起沟通科技术语,通过多种学术会议研讨两岸的语言文字和语言生
活问题。这些都促进了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之间的全方位接触,相互吸收,汉民族共同语的分化趋势得到
遏制,出现了再度整合的发展趋向。
汉民族共同语的再度整合,意义重大。第一,共同语之间的分歧受到政界、学界的正视。人们开始
自觉梳理语言分歧,分析其成因,评估其影响,寻觅“求同缩异”之法,无论是语言意识上还是语言生活
中,共同语的分歧都明显减少,由分化转向整合。第二,海外华语的发展具有了向心力,“普通话圈”与
“老国语圈”交集加大,逐渐重合,带动了世界华人语言也由分化转向整合(周清海,2016)。第三,汉语国
际教育也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和合作性,有利于在教材、师资、考试等方面实现两岸及国际合作,有利于汉
语的国际传播和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应用(周明朗,2017)。
王理嘉(2003,P142)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它以北京音系作为标准
音。”之所以认定国语和普通话都是民族共同语,还因为民族共同语带有一定“想象性”。现实中,由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共同语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核心,具有各种语言成分上的分歧,甚至共同语还使用不同的
称名和不同的书写系统,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可能使用不同的字母形体和不同的字母表,如印地语与
乌尔都语、中国的蒙古文与蒙古国的蒙古文等。共同语是有张力的,能够容忍各种分歧而不至于形成语
言分裂。这种张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语言分歧的大小、语言社团的认同等。语言分歧是客观
基础,但语言认同是决定共同语张力大小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普通话和台湾国语分离 70 年仍能再趋
近、再整合,根本原因来自于两岸的语言认同。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