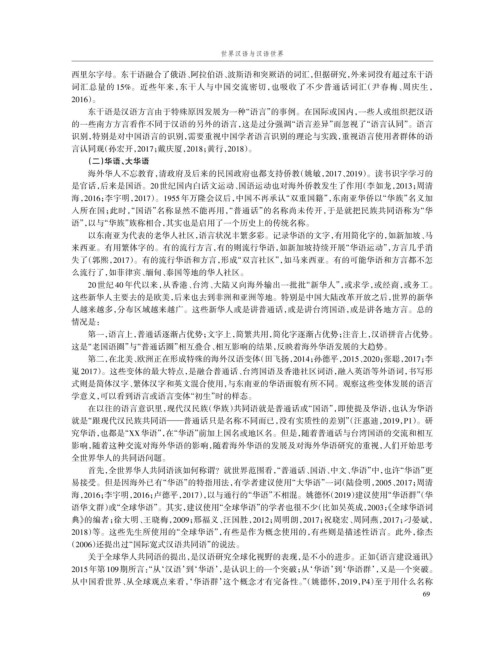Page 7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75
世界汉语与汉语世界
西里尔字母。东干语融合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但据研究,外来词没有超过东干语
词汇总量的 15%。近些年来,东干人与中国交流密切,也吸收了不少普通话词汇(尹春梅、周庆生,
2016)。
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由于特殊原因发展为一种“语言”的事例。在国际或国内,一些人或组织把汉语
的一些南方方言看作不同于汉语的另外的语言,这是过分强调“语言差异”而忽视了“语言认同”。语言
识别,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识别,需要重视中国学者语言识别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语言使用者群体的语
言认同观(孙宏开,2017;戴庆厦,2018;黄行,2018)。
(二)华语、大华语
海外华人不忘教育,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也都支持侨教(姚敏,2017、2019)。读书识字学习的
是官话,后来是国语。20世纪国内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也对海外侨教发生了作用(李如龙,2013;周清
海,2016;李宇明,2017)。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东南亚华侨以“华族”名义加
入所在国;此时,“国语”名称显然不能再用,“普通话”的名称尚未传开,于是就把民族共同语称为“华
语”,以与“华族”族称相合,其实也是启用了一个历史上的传统名称。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老华人社区,语言状况丰繁多彩。记录华语的文字,有用简化字的,如新加坡、马
来西亚。有用繁体字的。有的流行方言,有的则流行华语,如新加坡持续开展“华语运动”,方言几乎消
失了(郭熙,2017)。有的流行华语和方言,形成“双言社区”,如马来西亚。有的可能华语和方言都不怎
么流行了,如菲律宾、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人社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从香港、台湾、大陆又向海外输出一批批“新华人”,或求学,或经商,或务工。
这些新华人主要去的是欧美,后来也去到非洲和亚洲等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的新华
人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这些新华人或是讲普通话,或是讲台湾国语,或是讲各地方言。总的
情况是:
第一,语言上,普通话逐渐占优势;文字上,简繁共用,简化字逐渐占优势;注音上,汉语拼音占优势。
这是“老国语圈”与“普通话圈”相互叠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反映着海外华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在北美、欧洲正在形成特殊的海外汉语变体(田飞扬,2014;孙德平,2015、2020;张聪,2017;李
嵬 2017)。这些变体的最大特点,是融合普通话、台湾国语及香港社区词语,融入英语等外语词,书写形
式则是简体汉字、繁体汉字和英文混合使用,与东南亚的华语面貌有所不同。观察这些变体发展的语言
学意义,可以看到语言或语言变体“初生”时的样态。
在以往的语言意识里,现代汉民族(华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或“国语”,即使提及华语,也认为华语
就是“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汪惠迪,2019,P1)。研
究华语,也都是“XX华语”,在“华语”前加上国名或地区名。但是,随着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交流和相互
影响,随着这种交流对海外华语的影响,随着海外华语的发展及对海外华语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思考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问题。
首先,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该如何称谓?就世界范围看,“普通话、国语、中文、华语”中,也许“华语”更
易接受。但是因海外已有“华语”的特指用法,有学者建议使用“大华语”一词(陆俭明,2005、2017;周清
海,2016;李宇明,2016;卢德平,2017),以与通行的“华语”不相混。姚德怀(2019)建议使用“华语群”(华
语华文群)或“全球华语”。其实,建议使用“全球华语”的学者也很不少(比如吴英成,2003;《全球华语词
典》的编者;徐大明、王晓梅,2009;邢福义、汪国胜,2012;周明朗,2017;祝晓宏、周同燕,2017;刁晏斌,
2018)等。这些先生所使用的“全球华语”,有些是作为概念使用的,有些则是描述性语言。此外,徐杰
(2006)还提出过“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的说法。
关于全球华人共同语的提出,是汉语研究全球化视野的表现,是不小的进步。正如《语言建设通讯》
2015年第 109期所言:“从‘汉语’到‘华语’,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从‘华语’到‘华语群’,又是一个突破。
从中国看世界、从全球观点来看,‘华语群’这个概念才有完备性。”(姚德怀,2019,P4)至于用什么名称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