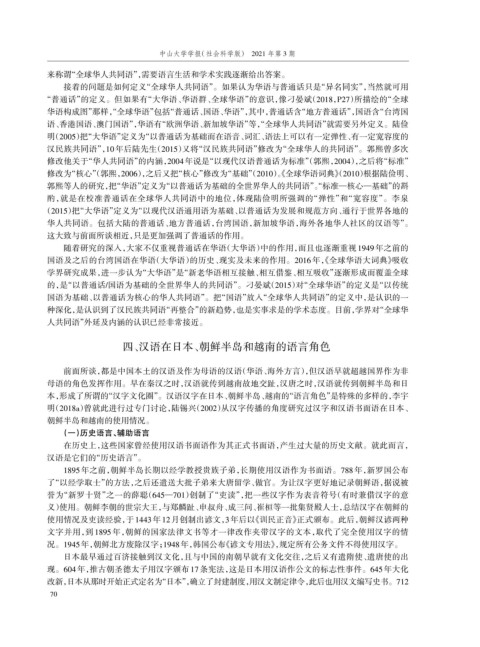Page 7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76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来称谓“全球华人共同语”,需要语言生活和学术实践逐渐给出答案。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全球华人共同语”。如果认为华语与普通话只是“异名同实”,当然就可用
“普通话”的定义。但如果有“大华语、华语群、全球华语”的意识,像刁晏斌(2018,P27)所描绘的“全球
华语构成图”那样,“全球华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华语”,其中,普通话含“地方普通话”,国语含“台湾国
语、香港国语、澳门国语”,华语有“欧洲华语、新加坡华语”等,“全球华人共同语”就需要另外定义。陆俭
明(200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
汉民族共同语”,10 年后陆先生(2015)又将“汉民族共同语”修改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郭熙曾多次
修改他关于“华人共同语”的内涵,2004年说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郭熙,2004),之后将“标准”
修改为“核心”(郭熙,2006),之后又把“核心”修改为“基础”(2010)。《全球华语词典》(2010)根据陆俭明、
郭熙等人的研究,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标准—核心—基础”的斟
酌,就是在校准普通话在全球华人共同语中的地位,体现陆俭明所强调的“弹性”和“宽容度”。李泉
(201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现代汉语通用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发展和规范方向、通行于世界各地的
华人共同语。包括大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海外各地华人社区的汉语等”。
这大致与前面所谈相近,只是更加强调了普通话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不仅重视普通话在华语(大华语)中的作用,而且也逐渐重视 1949 年之前的
国语及之后的台湾国语在华语(大华语)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作用。2016 年,《全球华语大词典》吸收
学界研究成果,进一步认为“大华语”是“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而覆盖全球
的,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刁晏斌(2015)对“全球华语”的定义是“以传统
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把“国语”放入“全球华人共同语”的定义中,是认识的一
种深化,是认识到了汉民族共同语“再整合”的新趋势,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目前,学界对“全球华
人共同语”外延及内涵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
四、汉语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语言角色
前面所谈,都是中国本土的汉语及作为母语的汉语(华语、海外方言),但汉语早就超越国界作为非
母语的角色发挥作用。早在秦汉之时,汉语就传到越南故地交趾,汉唐之时,汉语就传到朝鲜半岛和日
本,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汉语汉字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的“语言角色”是特殊的多样的,李宇
明(2018a)曾就此进行过专门讨论,陆锡兴(2002)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研究过汉字和汉语书面语在日本、
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使用情况。
(一)历史语言、辅助语言
在历史上,这些国家曾经使用汉语书面语作为其正式书面语,产生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就此而言,
汉语是它们的“历史语言”。
1895 年之前,朝鲜半岛长期以经学教授贵族子弟,长期使用汉语作为书面语。788 年,新罗国公布
了“以经学取士”的方法,之后还遣送大批子弟来大唐留学、做官。为让汉字更好地记录朝鲜语,据说被
誉为“新罗十贤”之一的薛聪(645—701)创制了“吏读”,把一些汉字作为表音符号(有时兼借汉字的意
义)使用。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与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桓等一批集贤殿人士,总结汉字在朝鲜的
使用情况及吏读经验,于 1443年 12月创制出谚文,3年后以《训民正音》正式颁布。此后,朝鲜汉谚两种
文字并用,到 1895 年,朝鲜的国家法律文书等才一律改作夹带汉字的文本,取代了完全使用汉字的情
况。1945年,朝鲜北方废除汉字;1948年,韩国公布《谚文专用法》,规定所有公务文件不得使用汉字。
日本最早通过百济接触到汉文化,且与中国的南朝早就有文化交往,之后又有遣隋使、遣唐使的出
现。604年,推古朝圣德太子用汉字颁布 17条宪法,这是日本用汉语作公文的标志性事件。645年大化
改新,日本从那时开始正式定名为“日本”,确立了封建制度,用汉文制定律令,此后也用汉文编写史书。712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