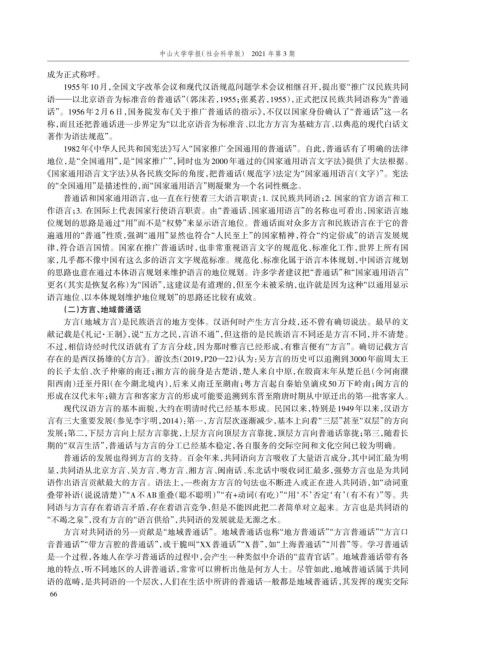Page 72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72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成为正式称呼。
1955年 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提出要“推广汉民族共同
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郭沫若,1955;张奚若,1955),正式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
话”。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不仅以国家身份确认了“普通话”这一名
称,而且还把普通话进一步界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自此,普通话有了明确的法律
地位,是“全国通用”,是“国家推广”,同时也为 2000 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供了大法根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各民族交际的角度,把普通话(规范字)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宪法
的“全国通用”是描述性的,而“国家通用语言”则凝聚为一个名词性概念。
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也一直在行使着三大语言职责:1. 汉民族共同语;2. 国家的官方语言和工
作语言;3. 在国际上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由“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名称也可看出,国家语言地
位规划的思路是通过“用”而不是“权势”来显示语言地位。普通话面对众多方言和民族语言在于它的普
遍通用的“普通”性质,强调“通用”显然也符合“人民至上”的国家精神,符合“约定俗成”的语言发展规
律,符合语言国情。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世界上所有国
家,几乎都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规范化、标准化属于语言本体规划,中国语言规划
的思路也意在通过本体语言规划来维护语言的地位规划。许多学者建议把“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
更名(其实是恢复名称)为“国语”,这建议是有道理的,但至今未被采纳,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以通用显示
语言地位、以本体规划维护地位规划”的思路还比较有成效。
(二)方言、地域普通话
方言(地域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汉语何时产生方言分歧,还不曾有确切说法。最早的文
献记载是《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但这指的是民族语言不同还是方言不同,并不清楚。
不过,相信诗经时代汉语就有了方言分歧,因为那时雅言已经形成,有雅言便有“方言”。确切记载方言
存在的是西汉扬雄的《方言》。游汝杰(2019,P20—22)认为:吴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0年前周太王
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的南迁;湘方言的前身是古楚语,楚人来自中原,在殷商末年从楚丘邑(今河南濮
阳西南)迁至丹阳(在今湖北境内),后来又南迁至湖南;粤方言起自秦始皇谪戍 50 万下岭南;闽方言的
形成在汉代末年;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东晋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出的第一批客家人。
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大约在明清时代已经基本形成。民国以来,特别是 1949年以来,汉语方
言有三大重要发展(参见李宇明,2014):第一,方言层次逐渐减少,基本上向着“三层”甚至“双层”的方向
发展;第二,下层方言向上层方言靠拢,上层方言向顶层方言靠拢,顶层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第三,随着长
期的“双言生活”,普通话与方言的分工已经基本稳定,各自服务的交际空间和文化空间已较为明确。
普通话的发展也得到方言的支持。百余年来,共同语向方言吸收了大量语言成分,其中词汇最为明
显,共同语从北京方言、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闽南话、东北话中吸收词汇最多,强势方言也是为共同
语作出语言贡献最大的方言。语法上,一些南方方言的句法也不断进入或正在进入共同语,如“动词重
叠带补语(说说清楚)”“A 不 AB 重叠(聪不聪明)”“有+动词(有吃)”“用‘不’否定‘有’(有不有)”等。共
同语与方言存在着语言矛盾,存在着语言竞争,但是不能因此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方言也是共同语的
“不竭之泉”,没有方言的“语言供给”,共同语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方言对共同语的另一贡献是“地域普通话”。地域普通话也称“地方普通话”“方言普通话”“方言口
音普通话”“带方言腔的普通话”,或干脆叫“XX普通话”“X普”,如“上海普通话”“川普”等。学习普通话
是一个过程,各地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类似中介语的“蓝青官话”。地域普通话带有各
地的特点,听不同地区的人讲普通话,常常可以辨析出他是何方人士。尽管如此,地域普通话属于共同
语的范畴,是共同语的一个层次,人们在生活中所讲的普通话一般都是地域普通话,其发挥的现实交际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