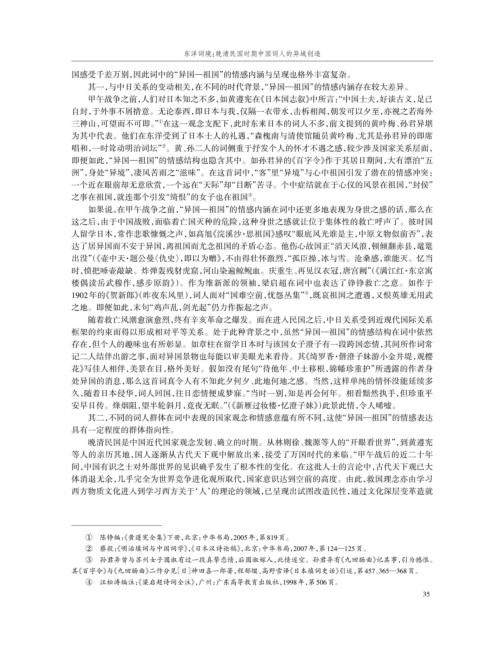Page 4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41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国感受千差万别,因此词中的“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与呈现也格外丰富复杂。
“
其一,与中日关系的变动相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存在较大差异。
甲午战争之前,人们对日本知之不多,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所言:“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
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
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在这一观念支配下,此时东来日本的词人不多,前文提到的黄吟梅、孙君异堪
①
为其中代表。他们在东洋受到了日本士人的礼遇,“森槐南与清使馆随员黄吟梅、尤其是孙君异的即席
唱和,一时耸动明治词坛”。黄、孙二人的词侧重于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较少涉及国家关系层面,
②
即便如此,“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也隐含其中。如孙君异的《百字令》作于其居日期间,大有漂泊“五
洲”,身处“异境”,凄风苦雨之“滋味”。在这首词中,“客”里“异境”与心中祖国引发了潜在的情感冲突:
一个近在眼前却无意欣赏,一个远在“天际”却“目断”苦寻。个中症结就在于心仪的风景在祖国,“封侯”
之事在祖国,就连那个引发“绮恨”的女子也在祖国 。
③
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在词中还更多地表现为身世之感的话,那么在
这之后,由于中国战败,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身世之感就让位于集体性的救亡呼声了。彼时国
人留学日本,常作悲歌慷慨之声,如高旭《浣溪沙·思祖国》感叹“眼底风光谁是主,中原文物似前否”,表
达了居异国而不安于异国,离祖国而尤念祖国的矛盾心态。他伤心故国正“滔天风浪,顿倾翻赤县,鼋鼍
出没”(《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不由得壮怀激烈,“孤臣操,冰与雪。沧桑感,谁能灭。忆当
时,愤把唾壶敲缺。炸弹轰残豺虎窟,河山染遍鲸鲵血。庆重生、再见汉衣冠,唐宫阙”(《满江红·东京寓
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词中也表达了铮铮救亡之意。如作于
1902年的《贺新郎》(昨夜东风里),词人面对“国难空前,忧怨丛集”,既哀祖国之遭遇,又恨英雄无用武
④
之地。即便如此,末句“鸡声乱,剑光起”仍力作振起之声。
随着救亡风潮愈演愈烈,终有辛亥革命之爆发。而在进入民国之后,中日关系受到近现代国际关系
框架的约束而得以形成相对平等关系。处于此种背景之中,虽然“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在词中依然
存在,但个人的趣味也有所彰显。如章柱在留学日本时与该国女子澄子有一段跨国恋情,其间所作词常
记二人结伴出游之事,面对异国景物也每能以审美眼光来看待。其《绮罗香·偕澄子妹游小金井堤,观樱
花》写佳人相伴,美景在目,格外美好。假如没有尾句“待他年、中土移根,锦幡珍重护”所透露的作者身
处异国的消息,那么这首词真令人有不知此夕何夕、此地何地之感。当然,这样单纯的情怀没能延续多
久,随着日本侵华,词人回国,往日恋情便成梦寐。“当时一别,知是再会何年。相看黯然执手,但珍重平
安早日传。烽烟阻,望半轮斜月,竟夜无眠。”(《新雁过妆楼·忆澄子妹》)此景此情,令人唏嘘。
其二,不同的词人群体在词中表现的国家观念和情感意蕴有所不同,这使“异国—祖国”的情感表达
具有一定程度的群体指向性。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轫、确立的时期。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到黄遵宪
等人的亲历其地,国人逐渐从古代天下观中解放出来,接受了万国时代的来临。“甲午战后的近二十年
间,中国有识之士对外部世界的见识确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批人士的言论中,古代天下观已大
体消退无余,几乎完全为世界竞争进化观所取代,国家意识达到空前的高度。由此,救国理念亦由学习
西方物质文化进入到学习西方关于‘人’的理论的领域,已呈现出试图改造民性,通过文化深层变革造就
①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19页。
② 蔡毅:《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日本汉诗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125页。
③ 孙君异曾与苏州女子圆淑有过一段真挚恋情,后圆淑嫁人,此情遂空。孙君异有《九回肠曲》记其事,引为憾恨。
其《百字令》与《九回肠曲》二作分见[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缀、高野雪译《日本填词史话》引述,第457、365—368页。
④ 汪松涛编注:《梁启超诗词全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