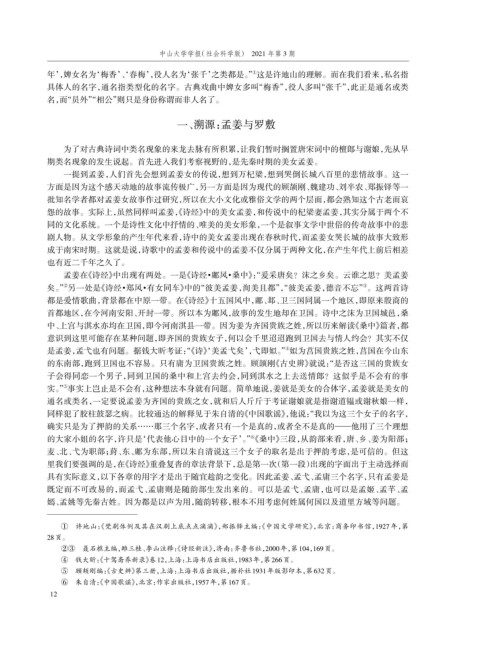Page 1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年’,婢女名为‘梅香’、‘春梅’,役人名为‘张千’之类都是。”这是许地山的理解。而在我们看来,私名指
①
具体人的名字,通名指类型化的名字。古典戏曲中婢女多叫“梅香”,役人多叫“张千”,此正是通名或类
名,而“员外”“相公”则只是身份称谓而非人名了。
一、溯源:孟姜与罗敷
为了对古典诗词中类名现象的来龙去脉有所积累,让我们暂时搁置唐宋词中的檀郎与谢娘,先从早
期类名现象的发生说起。首先进入我们考察视野的,是先秦时期的美女孟姜。
一提到孟姜,人们首先会想到孟姜女的传说,想到万杞梁,想到哭倒长城八百里的悲情故事。这一
方面是因为这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流传极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的顾颉刚、魏建功、刘半农、郑振铎等一
批知名学者都对孟姜女故事作过研究,所以在大小文化或雅俗文学的两个层面,都会熟知这个古老而哀
怨的故事。实际上,虽然同样叫孟姜,《诗经》中的美女孟姜,和传说中的杞梁妻孟姜,其实分属于两个不
同的文化系统。一个是诗性文化中抒情的、唯美的美女形象,一个是叙事文学中世俗的传奇故事中的悲
剧人物。从文学形象的产生年代来看,诗中的美女孟姜出现在春秋时代,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大致形
成于南宋时期。这就是说,诗歌中的孟姜和传说中的孟姜不仅分属于两种文化,在产生年代上前后相差
也有近二千年之久了。
孟姜在《诗经》中出现有两处。一是《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
矣。”另一处是《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两首诗
②
③
都是爱情歌曲,背景都在中原一带。在《诗经》十五国风中,鄘、邶、卫三国同属一个地区,即原来殷商的
首都地区,在今河南安阳、开封一带。所以本为鄘风,故事的发生地却在卫国。诗中之沫为卫国城邑,桑
中、上宫与淇水亦均在卫国,即今河南淇县一带。因为姜为齐国贵族之姓,所以历来解读《桑中》篇者,都
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某种问题,即齐国的贵族女子,何以会千里迢迢跑到卫国去与情人约会?其实不仅
是孟姜,孟弋也有问题。据钱大昕考证:“《诗》‘美孟弋矣’,弋即姒。”姒为莒国贵族之姓,莒国在今山东
④
的东南部,跑到卫国也不容易。只有庸为卫国贵族之姓。顾颉刚《古史辨》就说:“是否这三国的贵族女
子会得同恋一个男子,同到卫国的桑中和上宫去约会,同到淇水之上去送情郎?这似乎是不会有的事
实。”事实上岂止是不会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简单地说,姜就是美女的合体字,孟姜就是美女的
⑤
通名或类名,一定要说孟姜为齐国的贵族之女,就和后人斤斤于考证谢娘就是指谢道韫或谢秋娘一样,
同样犯了胶柱鼓瑟之病。比较通达的解释见于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他说:“我以为这三个女子的名字,
确实只是为了押韵的关系……那三个名字,或者只有一个是真的,或者全不是真的——他用了三个理想
的大家小姐的名字,许只是‘代表他心目中的一个女子’。”《桑中》三段,从韵部来看,唐、乡、姜为阳部;
⑥
麦、北、弋为职部;葑、东、鄘为东部,所以朱自清说这三个女子的取名是出于押韵考虑,是可信的。但这
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诗经》重叠复沓的章法背景下,总是第一次(第一段)出现的字面出于主动选择而
具有实际意义,以下各章的用字才是出于随宜趁韵之变化。因此孟姜、孟弋、孟庸三个名字,只有孟姜是
既定而不可改易的,而孟弋、孟庸则是随韵部生发出来的。可以是孟弋、孟庸,也可以是孟姬、孟芊、孟
嫣、孟姚等先秦古姓。因为都是以声为用,随韵转移,根本不用考虑何姓属何国以及道里方域等问题。
① 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年,第
28页。
②③ 聂石樵主编,雒三桂、李山注释:《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04,169页。
④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66页。
⑤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朴社1931年版影印本,第632页。
⑥ 朱自清:《中国歌谣》,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