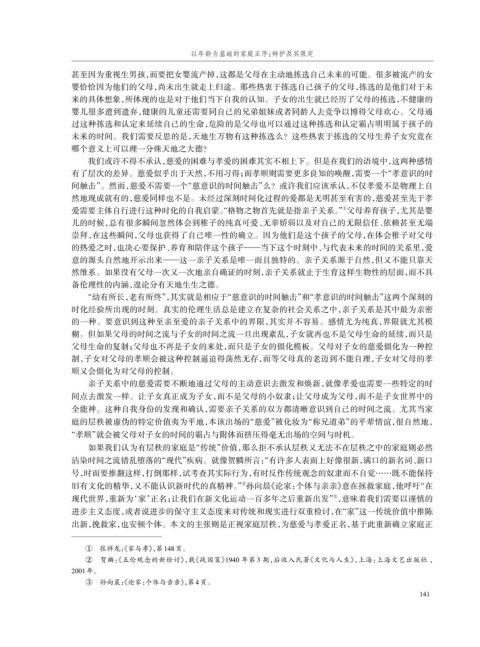Page 147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47
以年龄为基础的家庭正序:辩护及其限定
甚至因为重视生男孩,而要把女婴流产掉,这都是父母在主动地拣选自己未来的可能。很多被流产的女
婴恰恰因为他们的父母,尚未出生就走上归途。那些热衷于拣选自己孩子的父母,拣选的是他们对于未
来的具体想象,所体现的也是对于他们当下自我的认知。子女的出生就已经历了父母的拣选,不健康的
婴儿很多遭到遗弃,健康的儿童还需要同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同龄人去竞争以博得父母欢心。父母通
过这种拣选和认定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危险的是父母也可以通过这种拣选和认定霸占明明属于孩子的
未来的时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天地生万物有这种拣选么?这些热衷于拣选的父母生养子女究竟在
哪个意义上可以理一分殊天地之大德?
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慈爱的困难与孝爱的困难其实不相上下。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两种感情
有了层次的差异。慈爱似乎出于天然,不用习得;而孝顺则需要更多良知的唤醒,需要一个“孝意识的时
间触击”。然而,慈爱不需要一个“慈意识的时间触击”么?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不仅孝爱不是物理上自
然地现成就有的,慈爱同样也不是。未经过深刻时间化过程的爱都是无明甚至有害的,慈爱甚至先于孝
爱需要主体自行进行这种时化的自我启蒙。“格物之物首先就是指亲子关系。”父母养育孩子,尤其是婴
①
儿的时候,总有很多瞬间忽然体会到稚子的纯真可爱、无辜娇弱以及对自己的无限信任、依赖甚至无端
崇拜,在这些瞬间,父母也获得了自己唯一性的确立。因为他们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在体会稚子对父母
的热爱之时,也决心要保护、养育和陪伴这个孩子——当下这个时刻中、与代表未来的时间的关系里,爱
意的源头自然地开示出来——这一亲子关系是唯一而且独特的。亲子关系源于自然,但又不能只靠天
然维系。如果没有父母一次又一次地亲自确证的时刻,亲子关系就止于生育这样生物性的层面,而不具
备伦理性的内涵,遑论分有天地生生之德。
“幼有所长,老有所终”,其实就是相应于“慈意识的时间触击”和“孝意识的时间触击”这两个深刻的
时化经验所出现的时刻。真实的伦理生活总是建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亲子关系是其中最为亲密
的一种。要意识到这种至亲至爱的亲子关系中的界限,其实并不容易。感情尤为纯真,界限就尤其模
糊。但如果父母的时间之流与子女的时间之流一旦出现紊乱,子女就再也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而只是
父母生命的复制;父母也不再是子女的来处,而只是子女的僵化模板。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僵化为一种控
制,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会被这种控制逼迫得荡然无存,而等父母真的老迈到不能自理,子女对父母的孝
顺又会僵化为对父母的控制。
亲子关系中的慈爱需要不断地通过父母的主动意识去激发和焕新,就像孝爱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时
间点去激发一样。让子女真正成为子女,而不是父母的小奴隶;让父母成为父母,而不是子女世界中的
全能神。这种自我身份的发现和确认,需要亲子关系的双方都清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之流。尤其当家
庭的层秩被虚伪的特定价值夷为平地,本该出场的“慈爱”被化妆为“称兄道弟”的平辈情谊,很自然地,
“孝顺”就会被父母对子女的时间的霸占与附体而挤压得毫无出场的空间与时机。
如果我们认为有层秩的家庭是“传统”价值,那么拒不承认层秩又无法不在层秩之中的家庭则必然
沾染时间之流错乱堕落的“现代”疾病。就像贺麟所言:“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
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查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既不能保持
旧有文化的精华,又不能认识新时代的真精神。”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意在拯救家庭,他呼吁“在
②
现代世界,重新为‘家’正名;让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出发”,意味着我们需要以谨慎的
③
进步主义态度,或者说进步的保守主义态度来对传统和现实进行双重检讨,在“家”这一传统价值中推陈
出新,挽救家,也安顿个体。本文的主张则是正视家庭层秩,为慈爱与孝爱正名,基于此重新确立家庭正
① 张祥龙:《家与孝》,第148页。
②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载《战国策》1940 年第 3 期,后收入氏著《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1年。
③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第4页。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