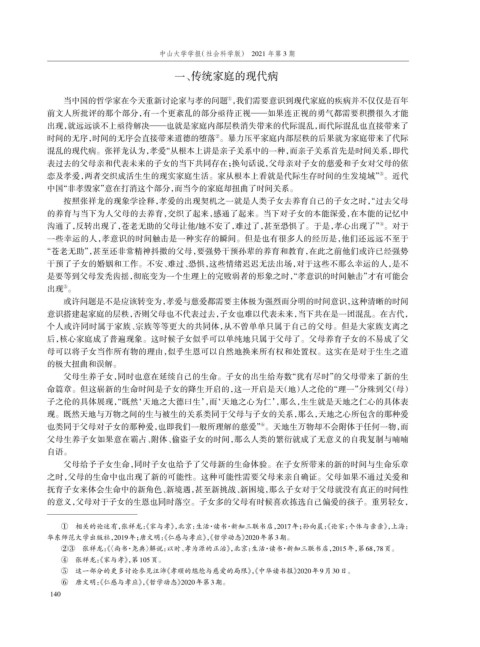Page 14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46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一、传统家庭的现代病
当中国的哲学家在今天重新讨论家与孝的问题 ,我们需要意识到现代家庭的疾病并不仅仅是百年
①
前文人所批评的那个部分,有一个更紊乱的部分亟待正视——如果连正视的勇气都需要积攒很久才能
出现,就远远谈不上亟待解决——也就是家庭内部层秩消失带来的代际混乱,而代际混乱也直接带来了
时间的无序,时间的无序会直接带来道德的堕落 。暴力压平家庭内部层秩的后果就为家庭带来了代际
②
混乱的现代病。张祥龙认为,孝爱“从根本上讲是亲子关系中的一种,而亲子关系首先是时间关系,即代
表过去的父母亲和代表未来的子女的当下共同存在;换句话说,父母亲对子女的慈爱和子女对父母的依
恋及孝爱,两者交织成活生生的现实家庭生活。家从根本上看就是代际生存时间的生发境域”。近代
③
中国“非孝毁家”意在打消这个部分,而当今的家庭却扭曲了时间关系。
按照张祥龙的现象学诠释,孝爱的出现契机之一就是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过去父母
的养育与当下为人父母的去养育,交织了起来,感通了起来。当下对子女的本能深爱,在本能的记忆中
沟通了,反转出现了,苍老无助的父母让他/她不安了,难过了,甚至恐惧了。于是,孝心出现了”。对于
④
一些幸运的人,孝意识的时间触击是一种实存的瞬间。但是也有很多人的经历是,他们还远远不至于
“苍老无助”,甚至还非常精神抖擞的父母,要强势干预孙辈的养育和教育,在此之前他们或许已经强势
干预了子女的婚姻和工作。不安、难过、恐惧,这些情绪迟迟无法出场,对于这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是不
是要等到父母发秃齿摇,彻底变为一个生理上的完败弱者的形象之时,“孝意识的时间触击”才有可能会
出现 。
⑤
或许问题是不是应该转变为,孝爱与慈爱都需要主体极为强烈而分明的时间意识,这种清晰的时间
意识搭建起家庭的层秩,否则父母也不代表过去,子女也难以代表未来,当下共在是一团混乱。在古代,
个人或许同时属于家族、宗族等等更大的共同体,从不曾单单只属于自己的父母。但是大家族支离之
后,核心家庭成了普遍现象。这时候子女似乎可以单纯地只属于父母了。父母养育子女的不易成了父
母可以将子女当作所有物的理由,似乎生恩可以自然地换来所有权和处置权。这实在是对于生生之道
的极大扭曲和误解。
父母生养子女,同时也意在延续自己的生命。子女的出生给寿数“犹有尽时”的父母带来了新的生
命篇章。但这崭新的生命时间是子女的降生开启的,这一开启是天(地)人之伦的“理一”分殊到父(母)
子之伦的具体展现,“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
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
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天地生万物却不会附体于任何一物,而
⑥
父母生养子女如果意在霸占、附体、偷盗子女的时间,那么人类的繁衍就成了无意义的自我复制与喃喃
自语。
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同时子女也给予了父母新的生命体验。在子女所带来的新的时间与生命乐章
之时,父母的生命中也出现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父母来亲自确证。父母如果不通过关爱和
抚育子女来体会生命中的新角色、新境遇,甚至新挑战、新困境,那么子女对于父母就没有真正的时间性
的意义,父母对于子女的生恩也同时落空。子女多的父母有时候喜欢拣选自己偏爱的孩子。重男轻女,
① 相关的论述有,张祥龙:《家与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②③ 张祥龙:《〈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68,78页。
④ 张祥龙:《家与孝》,第105页。
⑤ 这一部分的更多讨论参见汪沛《孝顺的尴尬与慈爱的局限》,《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30日。
⑥ 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