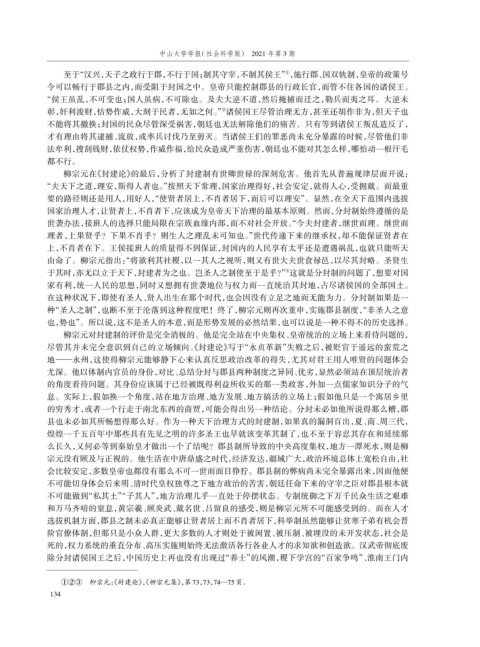Page 140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40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至于“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施行郡、国双轨制,皇帝的政策号
①
令可以畅行于郡县之内,而受阻于封国之中。皇帝只能控制郡县的行政长官,而管不住各国的诸侯王。
“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
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诸侯国王尽管治理无方,甚至还胡作非为,但天子也
②
不能将其撤换;封国的民众尽管深受祸害,朝廷也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有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了,
才有理由将其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乃至剪灭。当诸侯王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
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民众造成严重伤害,朝廷也不能对其怎么样,哪怕动一根汗毛
都不行。
柳宗元在《封建论》的最后,分析了封建制有世卿世禄的深刻危害。他首先从普遍规律层面开说: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按照天下常理,国家治理得好,社会安定,就得人心,受拥戴。而最重
要的路径则还是用人,用好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显然,在全天下范围内选拔
国家治理人才,让贤者上,不肖者下,应该成为皇帝天下治理的最基本原则。然而,分封制始终遵循的是
世袭办法,接班人的选择只能局限在宗族血缘内部,而不对社会开放。“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
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世代传递下来的继承权,却不能保证贤者在
上,不肖者在下。王侯接班人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封国内的人民享有太平还是遭遇祸乱,也就只能听天
由命了。柳宗元指出:“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
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这就是分封制的问题了,想要对国
③
家有利,统一人民的思想,同时又想拥有世袭地位与权力而一直统治其封地,占尽诸侯国的全部国土。
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有圣人、贤人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因没有立足之地而无能为力。分封制如果是一
种“圣人之制”,也断不至于沦落到这种程度吧!终了,柳宗元则再次重申,实施郡县制度,“非圣人之意
也,势也”。所以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不的历史选择。
柳宗元对封建制的评价是完全消极的。他是完全站在中央集权、皇帝统治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
尽管其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倾向。《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被贬官于遥远的蛮荒之
地——永州,这使得柳宗元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政治改革的得失,尤其对君王用人唯贤的问题体会
尤深。他以体制内官员的身份,对比、总结分封与郡县两种制度之异同、优劣,显然必须站在顶层统治者
的角度看待问题。其身份应该属于已经被既得利益所收买的那一类政客,外加一点儒家知识分子的气
息。实际上,假如换一个角度,站在地方治理、地方发展、地方搞活的立场上;假如他只是一个寓居乡里
的穷秀才,或者一个行走于南北东西的商贾,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分封未必如他所说得那么糟,郡
县也未必如其所畅想得那么好。作为一种天下治理方式的封建制,如果真的漏洞百出,夏、商、周三代,
煌煌一千五百年中那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许多圣王也早就该变革其制了,也不至于容忍其存在和延续那
么长久,又何必等到秦始皇才做出一个了结呢?郡县制所导致的中央高度集权,地方一潭死水,则是柳
宗元没有顾及与正视的。他生活在中唐鼎盛之时代,经济发达,疆域广大,政治环境总体上宽松自由,社
会比较安定,多数皇帝也都没有那么不可一世而面目狰狞。郡县制的弊病尚未完全暴露出来,因而他便
不可能切身体会后来明、清时代皇权独尊之下地方政治的苦害,朝廷任命下来的守宰之臣对郡县根本就
不可能做到“私其土”“子其人”,地方治理几乎一直处于停摆状态。专制统御之下万千民众生活之艰难
和万马齐喑的窒息,黄宗羲、顾炎武、戴名世、吕留良的感受,则是柳宗元所不可能感受到的。而在人才
选拔机制方面,郡县之制未必真正能够让贤者居上而不肖者居下,科举制虽然能够让贫寒子弟有机会晋
阶官僚体制,但那只是小众人群,更大多数的人才则处于被闲置、被压制、被埋没的未开发状态,社会是
死的,权力系统的垂直分布、高压实施则始终无法激活各行各业人才的求知欲和创造欲。汉武帝彻底废
除分封诸侯国王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养士”的风潮,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淮南王门内
①②③ 枊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第73,73,74—75页。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