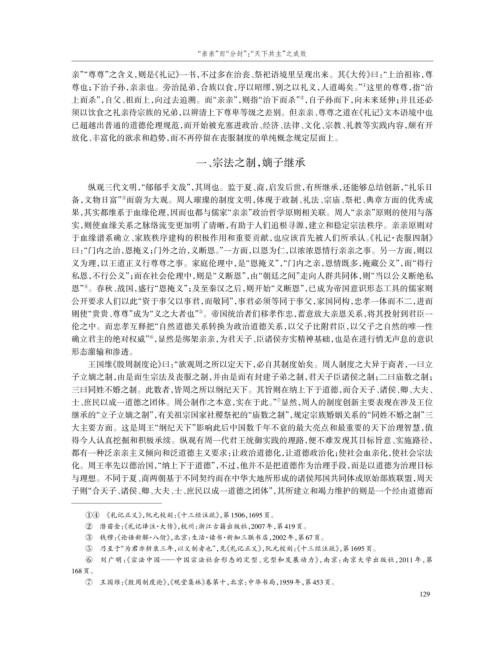Page 13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35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
亲”“尊尊”之含义,则是《礼记》一书,不过多在治丧、祭祀语境里呈现出来。其《大传》曰:“上治祖祢,尊
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这里的尊尊,指“治
①
上而杀”,自父、祖而上,向过去追溯。而“亲亲”,则指“治下而杀”,自子孙而下,向未来延伸;并且还必
②
须以饮食之礼亲待宗族的兄弟,以辨清上下尊卑等级之差别。但亲亲、尊尊之道在《礼记》文本语境中也
已超越出普通的道德伦理规范,而开始被充塞进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礼教等实践内容,颇有开
放化、丰富化的欲求和趋势,而不再停留在丧服制度的单纯概念规定层面上。
一、宗法之制,嫡子继承
纵观三代文明,“郁郁乎文哉”,其周也。监于夏、商,启发后世,有所继承,还能够总结创新,“礼乐日
备,文物日富”而蔚为大观。周人璀璨的制度文明,体现于政制、礼法、宗庙、祭祀、典章方面的优秀成
③
果,其实都维系于血缘伦理,因而也都与儒家“亲亲”政治哲学原则相关联。周人“亲亲”原则的使用与落
实,则使血缘关系之脉络流变更加明了清晰,有助于人们追根寻源,建立和稳定宗法秩序。亲亲原则对
于血缘谱系确立、家族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也应该首先被人们所承认。《礼记·丧服四制》
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一方面,以恩为仁,以浓浓恩情行亲亲之事。另一方面,则以
义为理,以王道正义行尊尊之事。家庭伦理中,是“恩掩义”,“门内之亲,恩情既多,掩藏公义”,而“得行
私恩,不行公义”;而在社会伦理中,则是“义断恩”,由“朝廷之间”走向人群共同体,则“当以公义断绝私
恩”。春秋、战国,盛行“恩掩义”;及至秦汉之后,则开始“义断恩”,已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工具的儒家则
④
公开要求人们以此“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君必须等同于事父,家国同构,忠孝一体而不二,进而
则使“贵贵、尊尊”成为“义之大者也”。帝国统治者们移孝作忠,蓄意放大亲恩关系,将其投射到君臣一
⑤
伦之中。而忠孝互释把“自然道德关系转换为政治道德关系,以父子比附君臣,以父子之自然的唯一性
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显然是绑架亲亲,为君天子、臣诸侯夯实精神基础,也是在进行悄无声息的意识
⑥
形态灌输和渗透。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曰:“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
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显然,周人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涉及王位
⑦
继承的“立子立嫡之制”,有关祖宗国家社稷祭祀的“庙数之制”,规定宗族婚姻关系的“同姓不婚之制”三
大主要方面。这是周王“纲纪天下”影响此后中国数千年不衰的最大亮点和最重要的天下治理智慧,值
得今人认真挖掘和积极承续。纵观有周一代君王统御实践的理路,便不难发现其目标旨意、实施路径,
都有一种泛亲亲主义倾向和泛道德主义要求: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社会血亲化,使社会宗法
化。周王率先以德治国,“纳上下于道德”,不过,他并不是把道德作为治理手段,而是以道德为治理目标
与理想。不同于夏、商两朝基于不同契约而在中华大地所形成的诸侯邦国共同体或原始部族联盟,周天
子则“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其所建立和竭力维护的则是一个经由道德而
①④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06,1695页。
② 潜苗金:《礼记译注·大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9页。
③ 钱穆:《论语新解·八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7页。
⑤ 乃至于“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见《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95页。
⑥ 刘广明:《宗法中国——中国宗法社会形态的定型、完型和发展动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68页。
⑦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3页。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