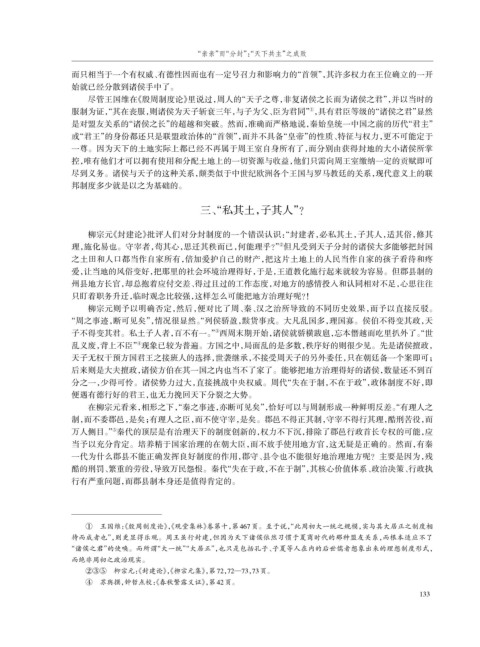Page 13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39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
而只相当于一个有权威、有德性因而也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首领”,其许多权力在王位确立的一开
始就已经分散到诸侯手中了。
尽管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说过,周人的“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并以当时的
服制为证,“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具有君臣等级的“诸侯之君”显然
①
是对盟友关系的“诸侯之长”的超越和突破。然而,准确而严格地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代“君主”
或“君王”的身份都还只是联盟政治体的“首领”,而并不具备“皇帝”的性质、特征与权力,更不可能定于
一尊。因为天下的土地实际上都已经不再属于周王室自身所有了,而分别由获得封地的大小诸侯所掌
控,唯有他们才可以拥有使用和分配土地上的一切资源与收益,他们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贡赋即可
尽到义务。诸侯与天子的这种关系,颇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联
邦制度多少就是以之为基础的。
三、“私其土,子其人”?
柳宗元《封建论》批评人们对分封制度的一个错误认识:“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
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但凡受到天子分封的诸侯大多能够把封国
②
之土田和人口都当作自家所有,倍加爱护自己的财产,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作自家的孩子看待和疼
爱,让当地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社会环境治理得好,于是,王道教化施行起来就较为容易。但郡县制的
州县地方长官,却总抱着应付交差、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对地方的感情投入和认同相对不足,心思往往
只盯着职务升迁,临时观念比较强,这样怎么可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柳宗元则予以明确否定,然后,便对比了周、秦、汉之治所导致的不同历史效果,而予以直接反驳。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情况很显然。“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
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西周末期开始,诸侯就骄横跋扈,忘本僭越而吃里扒外了。“世
③
乱义废,背上不臣”现象已较为普遍。方国之中,局面乱的是多数,秩序好的则很少见。先是诸侯擅政,
④
天子无权干预方国君王之接班人的选择,世袭继承,不接受周天子的另外委任,只在朝廷备一个案即可;
后来则是大夫擅政,诸侯方伯在其一国之内也当不了家了。能够把地方治理得好的诸侯,数量还不到百
分之一,少得可怜。诸侯势力过大,直接挑战中央权威。周代“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政体制度不好,即
便遇有德行好的君王,也无力挽回天下分裂之大势。
在柳宗元看来,相形之下,“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恰好可以与周制形成一种鲜明反差。“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
万人侧目。”秦代的顶层是有治理天下的制度创新的,权力不下沉,排除了郡邑行政首长专权的可能,应
⑤
当予以充分肯定。培养精于国家治理的在朝大臣,而不放手使用地方官,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有秦
一代为什么郡县不能正确发挥良好制度的作用,郡守、县令也不能很好地治理地方呢?主要是因为,残
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导致万民怨恨。秦代“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核心价值体系、政治决策、行政执
行有严重问题,而郡县制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第十,第 467页。至于说,“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
待而成者也”,则更显得乐观。周王虽行封建,但因为天下诸侯依然习惯于夏商时代的那种盟友关系,而根本适应不了
“诸侯之君”的使唤。而所谓“大一统”“大居正”,也只是包括孔子、子夏等人在内的后世儒者想象出来的理想制度形式,
而绝非周初之政治现实。
②③⑤ 枊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第72,72—73,73页。
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42页。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