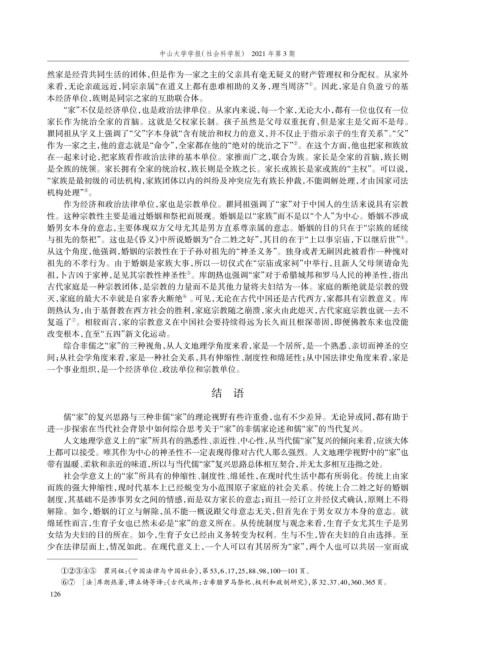Page 132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32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然家是经营共同生活的团体,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具有毫无疑义的财产管理权和分配权。从家外
来看,无论亲疏远近,同宗亲属“在道义上都有患难相助的义务,理当周济”。因此,家是自负盈亏的基
①
本经济单位,族则是同宗之家的互助联合体。
“家”不仅是经济单位,也是政治法律单位。从家内来说,每一个家,无论大小,都有一位也仅有一位
家长作为统治全家的首脑。这就是父权家长制。孩子虽然是父母双重抚育,但是家主是父而不是母。
瞿同祖从字义上强调了“父”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父”
作为一家之主,他的意志就是“命令”,全家都在他的“绝对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方面,他也把家和族放
②
在一起来讨论,把家族看作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家推而广之,联合为族。家长是全家的首脑,族长则
是全族的统领。家长拥有全家的统治权,族长则是全族之长。家长或族长是家或族的“主权”。可以说,
“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有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
机构处理”。
③
作为经济和政治法律单位,家也是宗教单位。瞿同祖强调了“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来说具有宗教
性。这种宗教性主要是通过婚姻和祭祀而展现。婚姻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婚姻不涉成
婚男女本身的意志,主要体现双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直系尊亲属的意志。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
与祖先的祭祀”。这也是《昏义》中所说婚姻为“合二姓之好”,其目的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④
从这个角度,他强调,婚姻的宗教性在于子孙对祖先的“神圣义务”。独身或者无嗣因此被看作一种愧对
祖先的不孝行为。由于婚姻是家族大事,所以一切仪式在“宗庙或家祠”中举行,且新人父母须请命先
祖,卜吉凶于家神,足见其宗教性神圣性 。库朗热也强调“家”对于希腊城邦和罗马人民的神圣性,指出
⑤
古代家庭是一种宗教团体,是宗教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力量将夫妇结为一体。家庭的断绝就是宗教的毁
灭,家庭的最大不幸就是自家香火断绝 。可见,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家都具有宗教意义。库
⑥
朗热认为,由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胜利,家庭宗教随之崩溃,家火由此熄灭,古代家庭宗教也就一去不
复返了 。相较而言,家的宗教意义在中国社会要持续得远为长久而且根深蒂固,即便佛教东来也没能
⑦
改变根本,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综合非儒之“家”的三种视角,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看,家是一个居所,是一个熟悉、亲切而神圣的空
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家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伸缩性、制度性和绵延性;从中国法律史角度来看,家是
一个事业组织,是一个经济单位、政法单位和宗教单位。
结 语
儒“家”的复兴思路与三种非儒“家”的理论视野有些许重叠,也有不少差异。无论异或同,都有助于
进一步探索在当代社会背景中如何综合思考关于“家”的非儒家论述和儒“家”的当代复兴。
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家”所具有的熟悉性、亲近性、中心性,从当代儒“家”复兴的倾向来看,应该大体
上都可以接受。唯其作为中心的神圣性不一定表现得像对古代人那么强烈。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家”也
带有温暖、柔软和亲近的味道,所以与当代儒“家”复兴思路总体相互契合,并无太多相互违拗之处。
社会学意义上的“家”所具有的伸缩性、制度性、绵延性,在现时代生活中都有所弱化。传统上由家
而族的强大伸缩性,现时代基本上已经蜕变为小范围原子家庭的社会关系。传统上合二姓之好的婚姻
制度,其基础不是涉事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是双方家长的意志;而且一经订立并经仪式确认,原则上不得
解除。如今,婚姻的订立与解除,虽不能一概说跟父母意志无关,但首先在于男女双方本身的意志。就
绵延性而言,生育子女也已然未必是“家”的意义所在。从传统制度与观念来看,生育子女尤其生子是男
女结为夫妇的目的所在。如今,生育子女已经由义务转变为权利。生与不生,皆在夫妇的自由选择。至
少在法律层面上,情况如此。在现代意义上,一个人可以有其居所为“家”,两个人也可以共居一室而成
①②③④⑤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53,6、17,25,88、98,100—101页。
⑥⑦ [法]库朗热著,谭立铸等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第32、37、40,360、365页。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