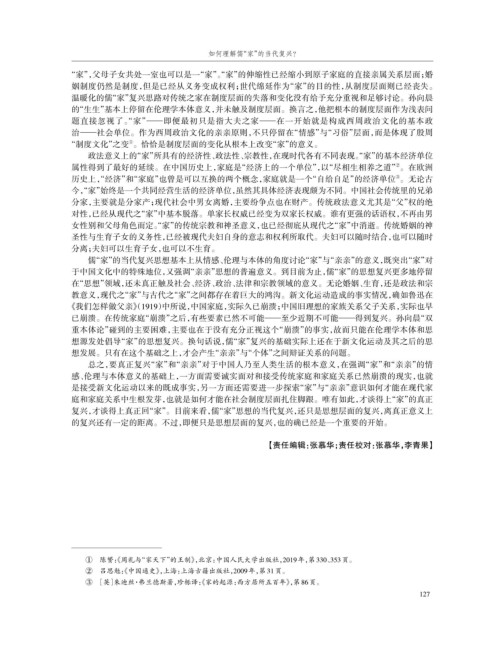Page 13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33
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
“家”,父母子女共处一室也可以是一“家”。“家”的伸缩性已经缩小到原子家庭的直接亲属关系层面;婚
姻制度仍然是制度,但是已经从义务变成权利;世代绵延作为“家”的目的性,从制度层面则已经丧失。
温暖化的儒“家”复兴思路对传统之家在制度层面的失落和变化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和足够讨论。孙向晨
的“生生”基本上停留在伦理学本体意义,并未触及制度层面。换言之,他把根本的制度层面作为浅表问
题直接忽视了。“家”——即便最初只是指大夫之家——在一开始就是构成西周政治文化的基本政
治——社会单位。作为西周政治文化的亲亲原则,不只停留在“情感”与“习俗”层面,而是体现了殷周
“制度文化”之变 。恰恰是制度层面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家”的意义。
①
政法意义上的“家”所具有的经济性、政法性、宗教性,在现时代各有不同表现。“家”的基本经济单位
属性得到了最好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家庭是“经济上的一个单位”,以“尽相生相养之道”。在欧洲
②
历史上,“经济”和“家庭”也曾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家庭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无论古
③
今,“家”始终是一个共同经营生活的经济单位,虽然其具体经济表现颇为不同。中国社会传统里的兄弟
分家,主要就是分家产;现代社会中男女离婚,主要纷争点也在财产。传统政法意义尤其是“父”权的绝
对性,已经从现代之“家”中基本脱落。单家长权威已经变为双家长权威。谁有更强的话语权,不再由男
女性别和父母角色而定。“家”的传统宗教和神圣意义,也已经彻底从现代之“家”中消逝。传统婚姻的神
圣性与生育子女的义务性,已经被现代夫妇自身的意志和权利所取代。夫妇可以随时结合,也可以随时
分离;夫妇可以生育子女,也可以不生育。
儒“家”的当代复兴思想基本上从情感、伦理与本体的角度讨论“家”与“亲亲”的意义,既突出“家”对
于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又强调“亲亲”思想的普遍意义。到目前为止,儒“家”的思想复兴更多地停留
在“思想”领域,还未真正触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领域的意义。无论婚姻、生育,还是政法和宗
教意义,现代之“家”与古代之“家”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事实情况,确如鲁迅在
《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中所说,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实际也早
已崩溃。在传统家庭“崩溃”之后,有些要素已然不可能——至少近期不可能——得到复兴。孙向晨“双
重本体论”碰到的主要困难,主要也在于没有充分正视这个“崩溃”的事实,故而只能在伦理学本体和思
想源发处倡导“家”的思想复兴。换句话说,儒“家”复兴的基础实际上还在于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思
想发展。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会产生“亲亲”与“个体”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
总之,要真正复兴“家”和“亲亲”对于中国人乃至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在强调“家”和“亲亲”的情
感、伦理与本体意义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诚实面对和接受传统家庭和家庭关系已然崩溃的现实,也就
是接受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家”与“亲亲”意识如何才能在现代家
庭和家庭关系中生根发芽,也就是如何才能在社会制度层面扎住脚跟。唯有如此,才谈得上“家”的真正
复兴,才谈得上真正回“家”。目前来看,儒“家”思想的当代复兴,还只是思想层面的复兴,离真正意义上
的复兴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即便只是思想层面的复兴,也的确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① 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0、353页。
②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③ [英]朱迪丝·弗兰德斯著,珍栎译:《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第86页。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