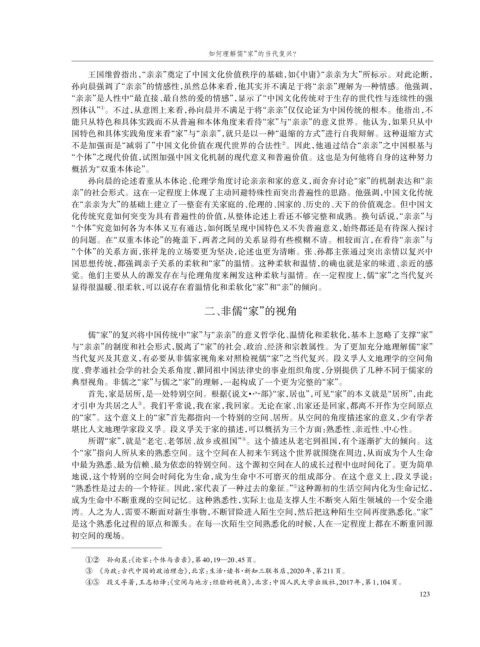Page 12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29
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
王国维曾指出,“亲亲”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秩序的基础,如《中庸》“亲亲为大”所标示。对此论断,
孙向晨强调了“亲亲”的情感性,虽然总体来看,他其实并不满足于将“亲亲”理解为一种情感。他强调,
“亲亲”是人性中“最直接、最自然的爱的情感”,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于生存的世代性与连续性的强
烈体认”。不过,从意图上来看,孙向晨并不满足于将“亲亲”仅仅论证为中国传统的根本。他指出,不
①
能只从特色和具体实践而不从普遍和本体角度来看待“家”与“亲亲”的意义世界。他认为,如果只从中
国特色和具体实践角度来看“家”与“亲亲”,就只是以一种“退缩的方式”进行自我辩解。这种退缩方式
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中国文化价值在现代世界的合法性 。因此,他通过结合“亲亲”之中国根基与
②
“个体”之现代价值,试图加强中国文化机制的现代意义和普遍价值。这也是为何他将自身的这种努力
概括为“双重本体论”。
孙向晨的论述着重从本体论、伦理学角度讨论亲亲和家的意义,而舍弃讨论“家”的机制表达和“亲
亲”的社会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动回避特殊性而突出普遍性的思路。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
在“亲亲为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家庭的、伦理的、国家的、历史的、天下的价值观念。但中国文
化传统究竟如何突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从整体论述上看还不够完整和成熟。换句话说,“亲亲”与
“个体”究竟如何各为本体又互有通达,如何既呈现中国特色又不失普遍意义,始终都还是有待深入探讨
的问题。在“双重本体论”的掩盖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相较而言,在看待“亲亲”与
“个体”的关系方面,张祥龙的立场要更为坚决,论述也更为清晰。张、孙都主张通过突出亲情以复兴中
国思想传统,都强调亲子关系的柔软和“家”的温情。这种柔软和温情,的确也就是家的味道、亲近的感
觉。他们主要从人的源发存在与伦理角度来阐发这种柔软与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儒“家”之当代复兴
显得很温暖、很柔软,可以说存在着温情化和柔软化“家”和“亲”的倾向。
二、非儒“家”的视角
儒“家”的复兴将中国传统中“家”与“亲亲”的意义哲学化、温情化和柔软化,基本上忽略了支撑“家”
与“亲亲”的制度和社会形式,脱离了“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属性。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儒“家”
当代复兴及其意义,有必要从非儒家视角来对照检视儒“家”之当代复兴。段义孚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角
度、费孝通社会学的社会关系角度、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事业组织角度,分别提供了几种不同于儒家的
典型视角。非儒之“家”与儒之“家”的理解,一起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家”。
首先,家是居所,是一处特别空间。根据《说文•宀部》“家,居也”,可见“家”的本义就是“居所”,由此
才引申为共居之人 。我们平常说,我在家,我回家。无论在家、出家还是回家,都离不开作为空间原点
③
的“家”。这个意义上的“家”首先都指向一个特别的空间、居所。从空间的角度描述家的意义,少有学者
堪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段义孚关于家的描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熟悉性、亲近性、中心性。
所谓“家”,就是“老宅、老邻居、故乡或祖国”。这个描述从老宅到祖国,有个逐渐扩大的倾向。这
④
个“家”指向人所从来的熟悉空间。这个空间在人初来乍到这个世界就围绕在周边,从而成为个人生命
中最为熟悉、最为信赖、最为依恋的特别空间。这个源初空间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时间化了。更为简单
地说,这个特别的空间会时间化为生命,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段义孚说:
“熟悉性是过去的一个特征。因此,家代表了一种过去的象征。”这种源初的生活空间内化为生命记忆,
⑤
成为生命中不断重现的空间记忆。这种熟悉性,实际上也是支撑人生不断突入陌生领域的一个安全港
湾。人之为人,需要不断面对新生事物,不断冒险进入陌生空间,然后把这种陌生空间再度熟悉化。“家”
是这个熟悉化过程的原点和源头。在每一次陌生空间熟悉化的时候,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在不断重回源
初空间的现场。
①②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第40,19—20、45页。
③ 《为政: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11页。
④⑤ 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4页。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