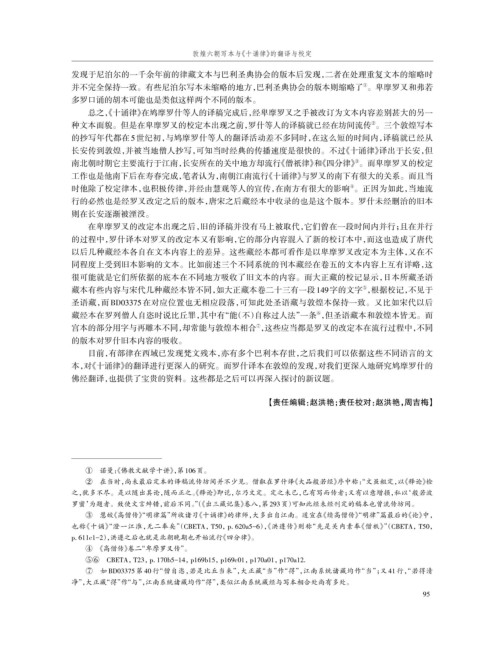Page 10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01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发现于尼泊尔的一千余年前的律藏文本与巴利圣典协会的版本后发现,二者在处理重复文本的缩略时
并不完全保持一致。有些尼泊尔写本未缩略的地方,巴利圣典协会的版本则缩略了 。卑摩罗叉和弗若
①
多罗口诵的胡本可能也是类似这样两个不同的版本。
总之,《十诵律》在鸠摩罗什等人的译稿完成后,经卑摩罗叉之手被改订为文本内容差别甚大的另一
种文本面貌。但是在卑摩罗叉的校定本出现之前,罗什等人的译稿就已经在坊间流传 。三个敦煌写本
②
的抄写年代都在 5 世纪初,与鸠摩罗什等人的翻译活动差不多同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译稿就已经从
长安传到敦煌,并被当地僧人抄写,可知当时经典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不过《十诵律》译出于长安,但
南北朝时期它主要流行于江南,长安所在的关中地方却流行《僧祇律》和《四分律》 。而卑摩罗叉的校定
③
工作也是他南下后在寿春完成,笔者认为,南朝江南流行《十诵律》与罗叉的南下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当
时他除了校定律本,也积极传律,并经由慧观等人的宣传,在南方有很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当地流
④
行的必然也是经罗叉改定之后的版本,唐宋之后藏经本中收录的也是这个版本。罗什未经删治的旧本
则在长安逐渐被湮没。
在卑摩罗叉的改定本出现之后,旧的译稿并没有马上被取代,它们曾在一段时间内并行;且在并行
的过程中,罗什译本对罗叉的改定本又有影响,它的部分内容混入了新的校订本中,而这也造成了唐代
以后几种藏经本各自在文本内容上的差异。这些藏经本都可看作是以卑摩罗叉改定本为主体,又在不
同程度上受到旧本影响的文本。比如前述三个不同系统的刊本藏经在卷五的文本内容上互有详略,这
很可能就是它们所依据的底本在不同地方吸收了旧文本的内容。而大正藏的校记显示,日本所藏圣语
藏本有些内容与宋代几种藏经本皆不同,如大正藏本卷二十三有一段 149字的文字 ,根据校记,不见于
⑤
圣语藏,而 BD03375 在对应位置也无相应段落,可知此处圣语藏与敦煌本保持一致。又比如宋代以后
藏经本在罗列僧人自恣时说比丘罪,其中有“能(不)自称过人法”一条 ,但圣语藏本和敦煌本皆无。而
⑥
宫本的部分用字与再雕本不同,却常能与敦煌本相合 ,这些应当都是罗叉的改定本在流行过程中,不同
⑦
的版本对罗什旧本内容的吸收。
目前,有部律在西域已发现梵文残本,亦有多个巴利本存世,之后我们可以依据这些不同语言的文
本,对《十诵律》的翻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罗什译本在敦煌的发现,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鸠摩罗什的
佛经翻译,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之后可以再深入探讨的新议题。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① 诺曼:《佛教文献学十讲》,第106页。
② 在当时,尚未最后定本的译稿流传坊间并不少见。僧叡在罗什译《大品般若经》序中称:“文虽粗定,以《释论》检
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即讫,尔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写而传者;又有以意增损,私以‘般若波
罗蜜’为题者。致使文言舛错,前后不同。”(《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3页)可知此经未经刊定的稿本也曾流传坊间。
③ 慧皎《高僧传》“明律篇”所收诸习《十诵律》的律师,大多出自江南。道宣在《续高僧传》“明律”篇最后的《论》中,
也称《十诵》“澄一江淮,无二奉矣”(CBETA,T50,p. 620a5-6),《洪遵传》则称“先是关内素奉《僧祇》”(CBETA,T50,
p. 611c1-2),洪遵之后也就是北朝晚期也开始流行《四分律》。
④ 《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
⑤⑥ CBETA,T23,p. 170b5-14,p169b15,p169c01,p170a01,p170a12.
⑦ 如 BD03375 第 40 行“僧自恣,若是比丘当来”,大正藏“当”作“得”,江南系统诸藏均作“当”;又 41 行,“若得清
净”,大正藏“得”作“与”,江南系统诸藏均作“得”,类似江南系统藏经与写本相合处尚有多处。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