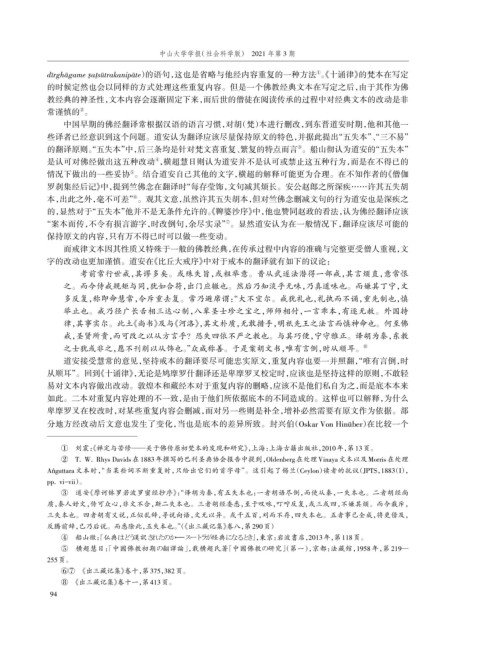Page 100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00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dīrghāgame ṣaṭsūtrakanipāte)的语句,这也是省略与他经内容重复的一种方法 。《十诵律》的梵本在写定
①
的时候定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重复内容。但是一个佛教经典文本在写定之后,由于其作为佛
教经典的神圣性,文本内容会逐渐固定下来,而后世的僧徒在阅读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典文本的改动是非
常谨慎的 。
②
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常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对胡(梵)本进行删改,到东晋道安时期,他和其他一
些译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道安认为翻译应该尽量保持原文的特色,并据此提出“五失本”、“三不易”
的翻译原则。“五失本”中,后三条均是针对梵文喜重复、繁复的特点而言 。船山彻认为道安的“五失本”
③
是认可对佛经做出这五种改动 ,横超慧日则认为道安并不是认可或禁止这五种行为,而是在不得已的
④
情况下做出的一些妥协 。结合道安自己其他的文字,横超的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在不知作者的《僧伽
⑤
罗刹集经后记》中,提到竺佛念在翻译时“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烦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许其五失胡
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观其文意,虽然许其五失胡本,但对竺佛念删减文句的行为道安也是深疾之
⑥
的,显然对于“五失本”他并不是无条件允许的。《鞞婆沙序》中,他也赞同赵政的看法,认为佛经翻译应该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显然道安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翻译应该尽可能的
⑦
保持原文的内容,只有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一些变动。
而戒律文本因其性质又特殊于一般的佛教经典,在传承过程中内容的准确与完整更受僧人重视,文
字的改动也更加谨慎。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对于戒本的翻译就有如下的议论:
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
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辙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真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
多反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
举止也。戒乃径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外国持
律,其事实尔。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
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
之士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 ⑧
道安接受慧常的意见,坚持戒本的翻译要尽可能忠实原文,重复内容也要一并照翻,“唯有言倒,时
从顺耳”。回到《十诵律》,无论是鸠摩罗什翻译还是卑摩罗叉校定时,应该也是坚持这样的原则,不敢轻
易对文本内容做出改动。敦煌本和藏经本对于重复内容的删略,应该不是他们私自为之,而是底本本来
如此。二本对重复内容处理的不一致,是由于他们所依据底本的不同造成的。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卑摩罗叉在校改时,对某些重复内容会删减,而对另一些则是补全,增补必然需要有原文作为依据。部
分地方经改动后文意也发生了变化,当也是底本的差异所致。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在比较一个
① 刘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② T. W. Rhys Davids 在 1883 年撰写的巴利圣典协会报告中提到,Oldenberg 在处理 Vinaya 文本以及 Morris 在处理
Aṅguttara 文本时,“当某些词不断重复时,只给出它们的首字母”。这引起了锡兰(Ceylon)读者的抗议(JPTS,1883(I),
pp. vi-vii)。
③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
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
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页)
④ 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118頁。
⑤ 横超慧日:「中國佛教初期の翻譯論」,载横超氏著『中國佛教の研究』(第一),京都:法藏館,1958 年,第 219—
255頁。
⑥⑦ 《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75,382页。
⑧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第413页。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