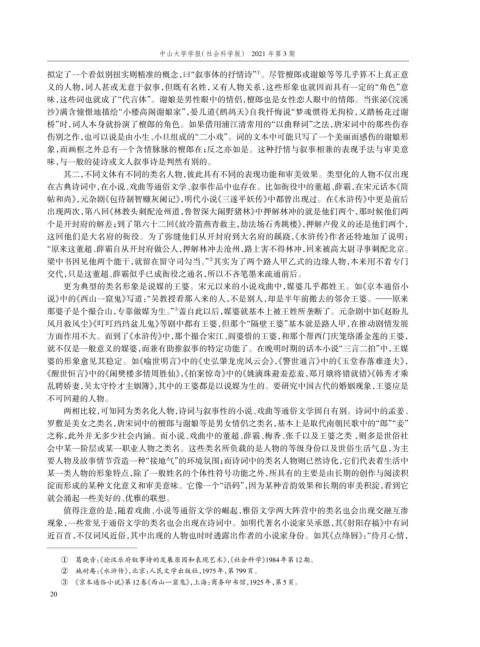Page 2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26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拟定了一个看似别扭实则精准的概念,曰“叙事体的抒情诗”。尽管檀郎或谢娘等等几乎算不上真正意
①
义的人物,词人甚或无意于叙事,但既有名姓,又有人物关系,这些形象也就因而具有一定的“角色”意
味,这些词也就成了“代言体”。谢娘是男性眼中的情侣,檀郎也是女性恋人眼中的情郎。当张泌《浣溪
沙》满含憧憬地描绘“小楼高阁谢娘家”,晏几道《鹧鸪天》自我忏悔说“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
桥”时,词人本身就扮演了檀郎的角色。如果借用浦江清常用的“以曲释词”之法,唐宋词中的那些伤春
伤别之作,也可以说是由小生、小旦组成的“二小戏”。词的文本中可能只写了一个美丽而感伤的谢娘形
象,而画框之外总有一个含情脉脉的檀郎在;反之亦如是。这种抒情与叙事相兼的表现手法与审美意
味,与一般的徒诗或文人叙事诗是判然有别的。
其二,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类名人物,彼此具有不同的表现功能和审美效果。类型化的人物不仅出现
在古典诗词中,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叙事作品中也存在。比如衙役中的董超、薛霸,在宋元话本《简
帖和尚》,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中都曾出现过。在《水浒传》中更是前后
出现两次,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押解林冲的就是他们两个,那时候他们两
个是开封府的解差;到了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押解卢俊义的还是他们两个,
这回他们是大名府的衙役。为了弥缝他们从开封府到大名府的蹊跷,《水浒传》作者还特地加了说明:
“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
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其实为了两个路人甲乙式的边缘人物,本来用不着专门
②
交代,只是这董超、薛霸似乎已成衙役之通名,所以不吝笔墨来疏通前后。
更为典型的类名形象是说媒的王婆。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媒婆几乎都姓王。如《京本通俗小
说》中的《西山一窟鬼》写道:“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原来
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盖自此以后,媒婆就基本上被王姓所垄断了。元杂剧中如《赵盼儿
③
风月救风尘》《叮叮珰珰盆儿鬼》等剧中都有王婆,但那个“隔壁王婆”基本就是路人甲,在推动剧情发展
方面作用不大。而到了《水浒传》中,那个撮合宋江、阎婆惜的王婆,和那个帮西门庆笼络潘金莲的王婆,
就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媒婆,而兼有助推叙事的特定功能了。在晚明时期的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王媒
婆的形象愈见其稳定。如《喻世明言》中的《史弘肇龙虎风云会》,《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
《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拍案惊奇》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韩秀才乘
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其中的王婆都是以说媒为生的。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现象,王婆应是
不可回避的人物。
两相比较,可知同为类名化人物,诗词与叙事性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固自有别。诗词中的孟姜、
罗敷是美女之类名,唐宋词中的檀郎与谢娘等是男女情侣之类名,基本上是取代南朝民歌中的“郎”“妾”
之称,此外并无多少社会内涵。而小说、戏曲中的董超、薛霸、梅香、张千以及王婆之类 ,则多是世俗社
会中某一阶层或某一职业人物之类名。这些类名所负载的是人物的等级身份以及世俗生活气息,为主
要人物及故事情节营造一种“接地气”的环境氛围;而诗词中的类名人物则已然诗化,它们代表着生活中
某一类人物的形象特点,除了一般姓名的个体性符号功能之外,所具有的主要是由长期的创作与阅读积
淀而形成的某种文化意义和审美意味。它像一个“语码”,因为某种音韵效果和长期的审美积淀,看到它
就会涌起一些美好的、优雅的联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崛起,雅俗文学两大阵营中的类名也会出现交融互渗
现象,一些常见于通俗文学的类名也会出现在诗词中。如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其《射阳存稿》中有词
近百首,不仅词风近俗,其中出现的人物也时时透露出作者的小说家身份。如其《点绛唇》:“待月心情,
① 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② 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799页。
③ 《京本通俗小说》第12卷《西山一窟鬼》,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页。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