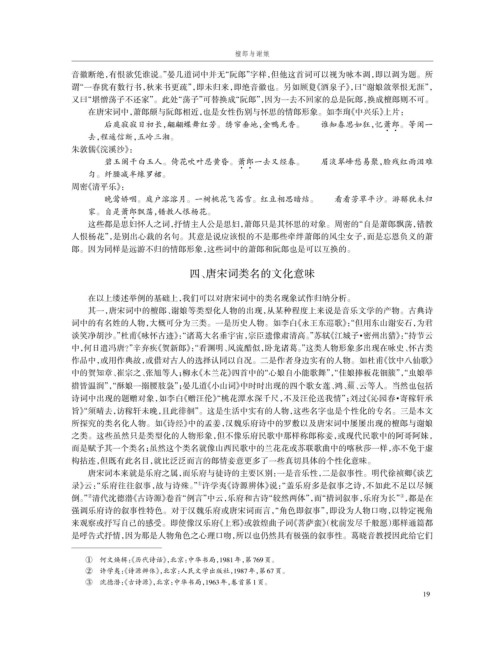Page 2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25
檀郎与谢娘
音徽断绝,有恨欲凭谁说。”晏几道词中并无“阮郎”字样,但他这首词可以视为咏本调,即以调为题。所
谓“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即未归来,即绝音徽也。另如顾敻《酒泉子》,曰“谢娘敛翠恨无涯”,
又曰“堪憎荡子不还家”。此处“荡子”可替换成“阮郎”,因为一去不回家的总是阮郎,换成檀郎则不可。
在唐宋词中,萧郎颇与阮郎相近,也是女性伤别与怀思的情郎形象。如李珣《中兴乐》上片:
后庭寂寂日初长,翩翩蝶舞红芳。绣帘垂地,金鸭无香。 谁知春思如狂,忆萧郎。等闲一
··
去,程遥信断,五岭三湘。
朱敦儒《浣溪沙》:
碧玉阑干白玉人。倚花吹叶忍黄昏。萧郎一去又经春。 眉淡翠峰愁易聚,脸残红雨泪难
··
匀。纤腰减半缘罗裙。
周密《清平乐》:
晚莺娇咽。庭户溶溶月。一树桃花飞茜雪。红豆相思暗结。 看看芳草平沙。游鞯犹未归
家。自是萧郎飘荡,错教人恨杨花。
··
这些都是思妇怀人之词,抒情主人公是思妇,萧郎只是其怀思的对象。周密的“自是萧郎飘荡,错教
人恨杨花”,是别出心裁的名句。其意是说应该恨的不是那些牵绊萧郎的风尘女子,而是忘恩负义的萧
郎。因为同样是远游不归的情郎形象,这些词中的萧郎和阮郎也是可以互换的。
四、唐宋词类名的文化意味
在以上缕述举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唐宋词中的类名现象试作归纳分析。
其一,唐宋词中的檀郎、谢娘等类型化人物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音乐文学的产物。古典诗
词中的有名姓的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人物。如李白《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
谈笑净胡沙。”杜甫《咏怀古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
中,何日遣冯唐?”辛弃疾《贺新郎》:“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这类人物形象多出现在咏史、怀古类
作品中,或用作典故,或借对古人的选择认同以自况。二是作者身边实有的人物。如杜甫《饮中八仙歌》
中的贺知章、崔宗之、张旭等人;柳永《木兰花》四首中的“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
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晏几道《小山词》中时时出现的四个歌女莲、鸿、 、云等人。当然也包括
诗词中出现的题赠对象,如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
旨》“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这是生活中实有的人物,这些名字也是个性化的专名。三是本文
所探究的类名化人物。如《诗经》中的孟姜,汉魏乐府诗中的罗敷以及唐宋词中屡屡出现的檀郎与谢娘
之类。这些虽然只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但不像乐府民歌中那样称郎称妾,或现代民歌中的阿哥阿妹,
而是赋予其一个类名;虽然这个类名就像山西民歌中的兰花花或苏联歌曲中的喀秋莎一样,亦不免于虚
构拈连,但既有此名目,就比泛泛而言的郎情妾意更多了一些真切具体的个性化意味。
唐宋词本来就是乐府之属,而乐府与徒诗的主要区别:一是音乐性,二是叙事性。明代徐祯卿《谈艺
录》云:“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许学夷《诗源辨体》说:“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
①
倒。”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首“例言”中云,乐府和古诗“较然两体”,而“措词叙事,乐府为长”,都是在
③
②
强调乐府诗的叙事性特色。对于汉魏乐府或唐宋词而言,“角色即叙事”,即设为人物口吻,以特定视角
来观察或抒写自己的感受。即使像汉乐府《上邪》或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那样通篇都
是呼告式抒情,因为那是人物角色之心理口吻,所以也仍然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葛晓音教授因此给它们
①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9页。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③ 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卷首第1页。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