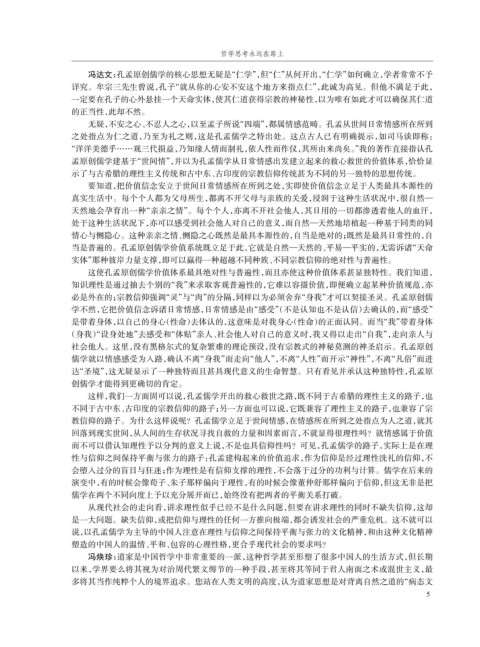Page 1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11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冯达文:孔孟原创儒学的核心思想无疑是“仁学”,但“仁”从何开出,“仁学”如何确立,学者常常不予
详究。牟宗三先生曾说,孔子“就从你的心安不安这个地方来指点仁”,此诚为高见。但他不满足于此,
一定要在孔子的心外悬挂一个天命实体,使其仁道获得宗教的神秘性,以为唯有如此才可以确保其仁道
的正当性,此却不然。
无疑,不安之心、不忍人之心,以至孟子所说“四端”,都属情感范畴。孔孟从世间日常情感所在所到
之处指点为仁之道,乃至为礼之则,这是孔孟儒学之特出处。这点古人已有明确提示,如司马谈即称:
“洋洋美德乎……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我的著作直接指认孔
孟原创儒学建基于“世间情”,并以为孔孟儒学从日常情感出发建立起来的救心救世的价值体系,恰恰显
示了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古中东、古印度的宗教信仰传统甚为不同的另一独特的思想传统。
要知道,把价值信念安立于世间日常情感所在所到之处,实即使价值信念立足于人类最具本源性的
真实生活中。每个个人都为父母所生,都离不开父母与亲族的关爱,浸润于这种生活状况中,很自然—
天然地会孕育出一种“亲亲之情”。每个个人,亦离不开社会他人,其日用的一切都渗透着他人的血汗,
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下,亦可以感受到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而自然—天然地培植起一种基于同类的同
情心与恻隐心。这种亲亲之情、恻隐之心既然是最具本源性的,自当是绝对的;既然是最具日常性的,自
当是普遍的。孔孟原创儒学价值系统既立足于此,它就是自然—天然的、平易—平实的,无需诉诸“天命
实体”那种彼岸力量支撑,即可以赢得一种超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绝对性与普遍性。
这使孔孟原创儒学价值体系最具绝对性与普遍性,而且亦使这种价值体系甚显独特性。我们知道,
知识理性是通过抽去个别的“我”来求取客观普遍性的,它难以容摄价值,即便确立起某种价值规范,亦
必是外在的;宗教信仰强调“灵”与“肉”的分隔,同样以为必须舍弃“身我”才可以契接圣灵。孔孟原创儒
学不然,它把价值信念诉诸日常情感,日常情感是由“感受”(不是认知也不是认信)去确认的,而“感受”
是带着身体,以自己的身心(性命)去体认的,这意味是对我身心(性命)的正面认同。而当“我”带着身体
(身我)“设身处地”去感受和“体贴”亲人、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时,我又得以走出“自我”,走向亲人与
社会他人。这里,没有黑格尔式的复杂繁难的理论预设,没有宗教式的神秘莫测的神圣启示。孔孟原创
儒学就以情感感受为入路,确认不离“身我”而走向“他人”,不离“人性”而开示“神性”,不离“凡俗”而进
达“圣境”,这无疑显示了一种独特而且甚具现代意义的生命智慧。只有看见并承认这种独特性,孔孟原
创儒学才能得到更确切的肯定。
这样,我们一方面固可以说,孔孟儒学开出的救心救世之路,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路子,也
不同于古中东、古印度的宗教信仰的路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既兼容了理性主义的路子,也兼容了宗
教信仰的路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孟儒学立足于世间情感,在情感所在所到之处指点为人之道,就其
回落到现实世间,从人间的生存状况寻找自救的力量和因素而言,不就显得很理性吗?就情感属于价值
而不可以借认知理性予以分判的意义上说,不是也具信仰性吗?可见,孔孟儒学的路子,实际上是在理
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路子:孔孟建构起来的价值追求,作为信仰是经过理性洗礼的信仰,不
会堕入过分的盲目与狂迷;作为理性是有信仰支撑的理性,不会落于过分的功利与计算。儒学在后来的
演变中,有的时候会像荀子、朱子那样偏向于理性,有的时候会像董仲舒那样偏向于信仰,但这无非是把
儒学在两个不同向度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已,始终没有把两者的平衡关系打破。
从现代社会的走向看,讲求理性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要在讲求理性的同时不缺失信仰,这却
是一大问题。缺失信仰,或把信仰与理性的任何一方推向极端,都会诱发社会的严重危机。这不就可以
说,以孔孟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人注意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文化精神,和由这种文化精神
塑造的中国人的温情、平和、包容的心理性格,更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吗?
冯焕珍:道家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派,这种哲学甚至形塑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长期
以来,学界要么将其视为对治周代繁文缛节的一种手段,甚至将其等同于君人南面之术或混世主义,最
多将其当作纯粹个人的境界追求。您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认为道家思想是对背离自然之道的“病态文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