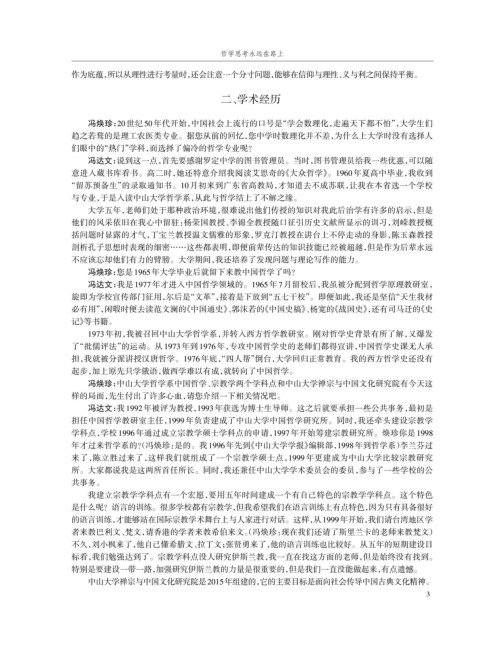Page 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9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作为底蕴,所以从理性进行考量时,还会注意一个分寸问题,能够在信仰与理性、义与利之间保持平衡。
二、学术经历
冯焕珍: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学生们
趋之若鹜的是理工农医类专业。据您从前的回忆,您中学时数理化并不差,为什么上大学时没有选择人
们眼中的“热门”学科,而选择了偏冷的哲学专业呢?
冯达文:说到这一点,首先要感谢罗定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图书管理员给我一些优惠,可以随
意进入藏书库看书。高二时,她还特意介绍我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60 年夏高中毕业,我收到
“留苏预备生”的录取通知书。10 月初来到广东省高教局,才知道去不成苏联,让我在本省选一个学校
与专业,于是入读中山大学哲学系,从此与哲学结上了不解之缘。
大学五年,老师们处于那种政治环境,很难说出他们传授的知识对我此后治学有许多的启示,但是
他们的风采依旧在我心中留驻:杨荣国教授、李锦全教授随口征引历史文献所显示的训习,刘嵘教授概
括问题时显露的才气,丁宝兰教授温文儒雅的形象,罗克汀教授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的身影,陈玉森教授
剖析孔子思想时表现的细密……这些都表明,即便前辈传达的知识技能已经被超越,但是作为后辈永远
不应该忘却他们有力的臂膀。大学期间,我还培养了发现问题与理论写作的能力。
冯焕珍:您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就留下来教中国哲学了吗?
冯达文:我是 1977年才进入中国哲学领域的。1965年 7月留校后,我虽被分配到哲学原理教研室,
旋即为学校宣传部门征用,尔后是“文革”,接着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天生我材
必有用”,闲暇时便去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杨宽的《战国史》,还有司马迁的《史
记》等书籍。
1973年初,我被召回中山大学哲学系,并转入西方哲学教研室。刚对哲学史背景有所了解,又爆发
了“批儒评法”的运动。从 1973年到 1976年,专攻中国哲学史的老师们都得宣讲,中国哲学史课无人承
担,我就被分派讲授汉唐哲学。1976年底,“四人帮”倒台,大学回归正常教育。我的西方哲学史还没有
起步,加上原先只学俄语,做西学难以有成,就转向了中国哲学。
冯焕珍: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宗教学两个学科点和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有今天这
样的局面,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冯达文:我 1992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获选为博士生导师。这之后就要承担一些公共事务,最初是
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99 年负责建成了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同时,我还牵头建设宗教学
学科点,学校 1996 年通过成立宗教学硕士学科点的申请,1997 年开始筹建宗教研究所。焕珍你是 1998
年才过来哲学系的?(冯焕珍:是的。我 1996年先到《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8年到哲学系)李兰芬过
来了,陈立胜过来了,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宗教学硕士点,1999 年更建成为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
所。大家都说我是这两所首任所长。同时,我还兼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一些学校的公
共事务。
我建立宗教学学科点有一个宏愿,要用五年时间建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宗教学学科点。这个特色
是什么呢?语言的训练。很多学校都有宗教学,但我希望我们在语言训练上有点特色,因为只有具备很好
的语言训练,才能够站在国际宗教学术舞台上与人家进行对话。这样,从1999年开始,我们请台湾地区学
者来教巴利文、梵文,请香港的学者来教希伯来文。(冯焕珍:现在我们还请了斯里兰卡的老师来教梵文)
不久,刘小枫来了,他自己懂希腊文、拉丁文;张贤勇来了,他的语言训练也比较好。从五年的短期建设目
标看,我们勉强达到了。宗教学科点没人研究伊斯兰教,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老师,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特别是要建设一带一路,加强研究伊斯兰教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一直没能做起来,有点遗憾。
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是2015年组建的,它的主要目标是面向社会传导中国古典文化精神。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