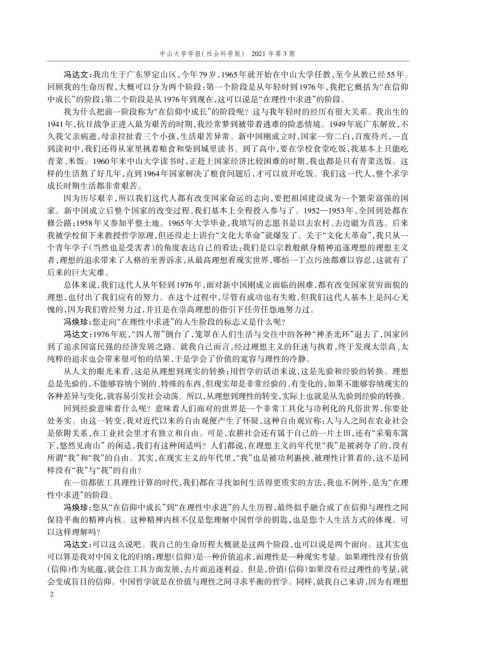Page 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P.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冯达文:我出生于广东罗定山区,今年 79 岁,1965 年就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至今从教已经 55 年。
回顾我的生命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年轻时到 1976 年,我把它概括为“在信仰
中成长”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76年到现在,这可以说是“在理性中求进”的阶段。
我为什么把前一阶段称为“在信仰中成长”的阶段呢?这与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出生的
1941年,抗日战争正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我经常梦到被带着逃难的险恶情境。1949年底广东解放,不
久我父亲病逝,母亲拉扯着三个小孩,生活艰苦异常。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直
到读初中,我们还得从家里挑着粮食和柴到城里读书。到了高中,要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基本上只能吃
青菜、米饭。1960年来中山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也都是只有青菜送饭。这
样的生活熬了好几年,直到 1964年国家解决了粮食问题后,才可以放开吃饭。我们这一代人,整个求学
成长时期生活都非常艰苦。
因为历尽艰辛,所以我们这代人都有改变国家命运的志向,要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
家。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的改变过程,我们基本上全程投入参与了。1952—1953 年,全国到处都在
修公路;1958年又参加平整土地。1965年大学毕业,我填写的志愿书是以去农村、去边疆为首选。后来
我被学校留下来教授哲学原理,但还没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我只从一
个青年学子(当然也是受害者)的角度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是以宗教般献身精神追逐理想的理想主义
者,理想的追求带来了人格的至善诉求,从最高理想看现实世界,哪怕一丁点污浊都难以容忍,这就有了
后来的巨大灾难。
总体来说,我们这代人从年轻到 1976年,面对新中国刚成立面临的困难,都有改变国家贫穷面貌的
理想,也付出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问心无
愧的,因为我们曾经努力过,并且是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下任劳任怨地努力过。
冯焕珍:您走向“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阶段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冯达文:1976 年底,“四人帮”倒台了,笼罩在人们生活与交往中的各种“神圣光环”退去了,国家回
到了追求国富民强的经济发展之路。就我自己而言,经过理想主义的狂迷与执着,终于发现太崇高、太
纯粹的追求也会带来很可怕的结果,于是学会了价值的宽容与理性的冷静。
从人文的眼光来看,这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用哲学的话语来说,这是先验和经验的转换。理想
总是先验的,不能够容纳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但现实却是非常经验的、有变化的,如果不能够容纳现实的
各种差异与变化,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从先验到经验的转换。
回到经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工具化与功利化的凡俗世界,你要处
处务实。由这一转变,我对近代以来的自由观便产生了怀疑,这种自由观宣称:人与人之间在农业社会
是依附关系,在工业社会里才有独立和自由。可是,农耕社会还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田,还有“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我们有这种闲适吗?人们都说,在理想主义的年代里“我”是被剥夺了的,没有
所谓“我”和“我”的自由。其实,在现实主义的年代里,“我”也是被功利裹挾、被理性计算着的,这不是同
样没有“我”与“我”的自由?
在一切都依工具理性计算的时代,我们都在寻找如何生活得更质实的方法,我也不例外,是为“在理
性中求进”的阶段。
冯焕珍:您从“在信仰中成长”到“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历程,最终似乎融合成了在信仰与理性之间
保持平衡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不仅是您理解中国哲学的钥匙,也是您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可
以这样理解吗?
冯达文:可以这么说吧。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大概就是这两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两个面向。这其实也
可以算是我对中国文化的归纳:理想(信仰)是一种价值追求,而理性是一种现实考量。如果理性没有价值
(信仰)作为底蕴,就会往工具方面发展,去片面追逐利益。但是,价值(信仰)如果没有经过理性的考量,就
会变成盲目的信仰。中国哲学就是在价值与理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哲学。同样,就我自己来讲,因为有理想
2